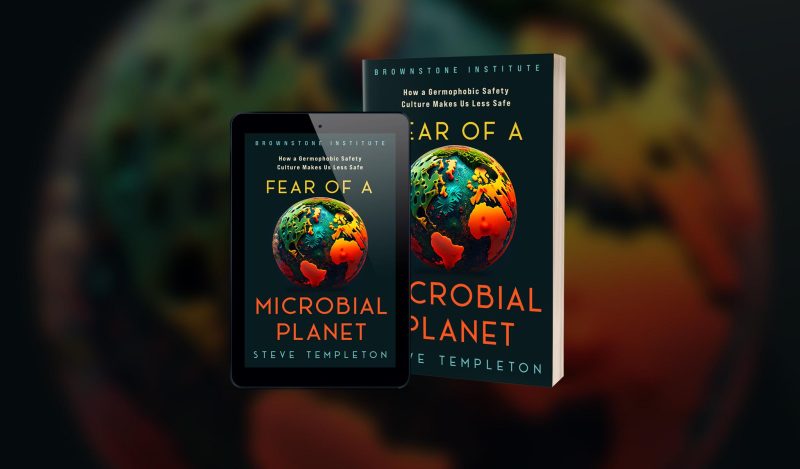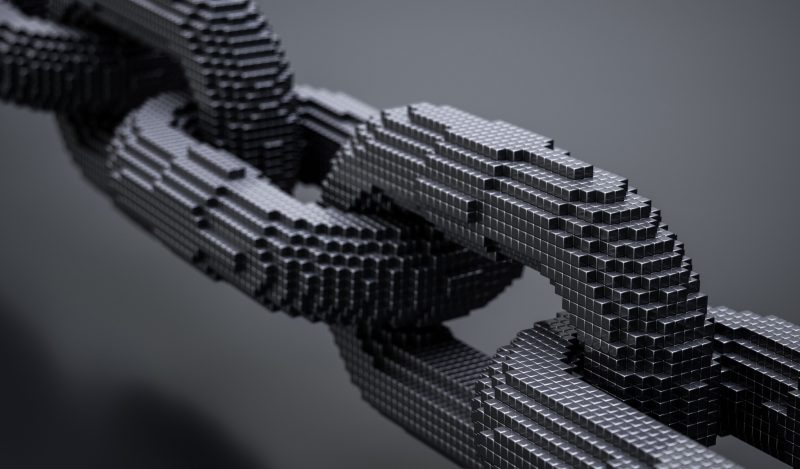11年2023月XNUMX日,拜登政府解除了最后的限制。 我们这些抵制冠状病毒的外国人终于可以再次前往美国了。 该制度的解释是什么? 为什么 Corona 政权可以如此轻易地维护自己,为什么同样的计划可以继续用于 Climate 和 Wokeness 政权?
至少从西欧的角度来看,最好的解释是:认为到 2020 年春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开放社会和一个共和宪政国家是一种错觉。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直到 1989 年盛行的反共叙事需要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和一个相对运作良好的法治。 随着这种叙事随着苏联帝国的崩溃而结束,因此可以预料,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叙事将取而代之,并扫除开放社会的支柱和作为分界线而存在的法治。苏联共产主义。
这是最好的解释,因为从它的角度来看,自 2020 年春季以来的发展并不令人惊讶,而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其结果是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即以中央国家机构掌握权力、立法和管辖权为特征的共和宪政国家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实现开放的适当手段。社会。
当从2020年XNUMX月开始,欧洲的政客们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的传播而提出封城的想法时,我认为如果政客们屈服于这种获得权力的诱惑,媒体和人民就会罢免他们:中国人极权主义不能适用于欧洲或美国。
当不仅个别城市被封锁,而且欧洲和美国的整个州都被封锁时,我认为这是一种恐慌反应。 恐慌肯定是故意激起的,尤其是那些应该保持冷静并依靠证据的人,即科学家、公务员和政治家。 然而,故意散布恐惧和 恐慌 无法解释我们自 2020 年春季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恐慌不会持续数年。
令人震惊的是,一些被媒体描绘成科学代言人的医学专家已经预测 2009-10 年将爆发猪流感大流行——例如美国的 Anthony Fauci、英国的 Neil Ferguson 和 Christian Drosten在德国。 当时,他们被及时制止了。
现在,他们准备得更好,协调性更强,并且拥有强大的盟友,例如比尔·盖茨和克劳斯·施瓦布。 然而,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什么秘密。 众所周知,这些人想要什么,他们提倡什么样的科学。 如果有人认为有一个 阴谋 在这里,那么人们必须简单地承认总是存在这样的阴谋。
像任何“阴谋”一样,这个阴谋也与利润利益密切相关。 然而,受封锁、检测、检疫和疫苗接种要求伤害的公司比从该制度中受益的公司多得多。 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这个政权,直接、明显地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并违背了他们过去与同胞打交道时的价值观和信念。
阴谋论甚至无法提供正确的诊断。 它把注意力从一个关键事实上移开:在应对冠状病毒浪潮时出现的相同行动模式也出现在其他问题上,例如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以及对据称受压迫的少数群体的偏爱(所谓的觉醒)。
总体模式是这样的:人们被普遍怀疑以其惯常的生活方式伤害他人——任何形式的直接社会接触,都可能助长有害病毒的传播; 任何形式的能源消耗都可能导致有害的气候变化; 对于任何形式的社会行为,一个人都可能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伤害历史上一直受压迫的少数群体的成员。 一个人不仅要服从对社会关系而且对私人生活的全面监管,才能消除这种普遍的怀疑。 该规定由政治当局强加并通过强制执行。 政治当局使用所谓的科学发现来使这项全面的监管合法化。
模式是一样的; 但推动各自问题(新冠、气候、觉醒)的人是不同的,即使存在重叠。 如果有一种行为模式在不同的主题中表现出来,那么这表明我们正在应对一个总体趋势。 弗拉芒心理学家马蒂亚斯·迪斯梅特在他的书的第二部分解释了 极权主义心理学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22)这种趋势如何形成以极权主义告终的群众运动,同样在 Brownstone,30 年 22 月 XNUMX 日)。 牛津学者爱德华·哈达斯 (Edward Hadas) 同一方向 在寻找对布朗斯通的解释时。
事实上,正如我在 较早的一块. 极权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公开的、人身暴力直至并包括灭绝整个人群。 极权统治的核心是一种所谓的科学学说,它利用国家权力来规范所有社会和私人生活。
这就是当前趋势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例如迄今为止的冠状病毒浪潮、气候变化和对某些少数群体的保护。 这些问题是偶然的。 它们取决于出现哪些实际挑战(病毒浪潮、气候变化),这些挑战可以用来推动这种包罗万象的社会控制制度的趋势。
相比之下,潜在趋势并不是偶然的。 至少以下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助长了这一趋势:
1) 政治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是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方法所发展出的知识可以涵盖一切,包括人类的思想和行动的学说。 当中央政府通过强制性政治措施控制人们的行为的要求源于对知识的要求时,科学主义就是政治性的。 “追随科学”是政治科学主义的口号。 政治科学主义将科学置于人权之上:所谓的科学使凌驾于基本权利之上的政治行为合法化。 “遵循科学”使用所谓的科学作为反对人们基本权利的武器。
2) 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自 1970 年代以来的一股思想潮流,它声称理性的使用不是普遍的,而是与特定的文化、宗教、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有关。这种相对化的结果是在社会和国家,平等权利不再适用于所有人,但某些群体将受到优待。 同样,在学术界,它不再只是相关的 什么 有人说,但主要是 谁 说它,这是有关人员的文化、宗教、种族、性别、性取向等。 结果是理性不再是限制权力行使的工具。 理性作为一种限制权力的工具,与理性使用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普遍性主张相得益彰。 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偏爱某些群体反对普遍使用理性,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因此它与后马克思主义(也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其特点是总能找到新的、所谓的受害者群体以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为原则的共和宪政国家。
3) 福利国家:现代宪政国家的合法化在于为所有人实施平等权利。 这意味着政治机构通过保护其领土上的每个人免受他人对生命、肢体和财产的攻击来保证安全。 为此,国家机关拥有 (i) 在各自领土上的武力垄断(行政权)和 (ii) 立法和管辖权(立法、司法)的垄断。 然而,这种权力的集中诱使其持有者——尤其是政治家——将保护的保障范围越来越广,以防止各种生命风险,最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可以防止病毒传播、气候变化并反对可能伤害某些声乐团体感情的观点(清醒)。 为了证明政治机构对保护和权力的要求的相应扩展是正当的,福利国家依赖于政治科学主义和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提供的叙述。
4) 权贵资本主义:鉴于上述权力以提供更多保护为借口集中在中央国家机构手中,企业家将其产品展示为对共同利益的贡献并要求国家支持是有利的。 结果是裙带资本主义:利润是私有的。 风险转移到国家身上,从而转移到那些国家可以以税收的形式征收强制性费用以在必要时使公司免于破产的人。 如果公司随后采用各自的政治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可以将这种商业模式推向极端:国家不仅将他们从亏损和资不抵债中解救出来,而且还直接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购买他们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正是依靠公众字面上是被迫的,而公司不对可能的损害承担责任。 我们已经通过电晕疫苗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变态。 它在所谓的可再生能源中重演。
电晕、气候和觉醒状态是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强大趋势的表现。 更准确地说,我们目睹的向特定后现代极权主义的过渡一方面依赖于福利国家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力量联盟,另一方面依赖于科学中的政治科学主义力量和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他。
然而,揭露和分析这一趋势只是对我们所见的诊断,而不是解释。 Corona、Climate 和 Wokeness 制度各由少数人推动。 为什么这少数人能够掀起一股潮流,让这么多人顺风顺水,以至于向新极权主义的过渡几乎没有阻力,尽管有所有历史经验?
开放社会与共和法治的错误
这种趋势是出人意料且无法解释的,前提是我们迄今大体上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个共和宪政国家。 卡尔·波普尔名著意义上的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945) 的特点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世界观等在其中和平共处,通过相互交流在经济(分工)和文化上相互丰富。 开放社会不是由任何关于实质性普遍利益的共同观念塑造的。 没有相应的叙述将社会团结在一起。 同样,法治:它强制每个人尊重所有其他人的自决权的道德义务。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冠状病毒浪潮并不比以往的呼吸道病毒浪潮更糟,例如 1957-58 年的亚洲流感和 1968-70 年的香港流感。 当人们查看经验证据时,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和透明。 为什么当时没有考虑采取强制性政治措施来对抗这些过去的病毒爆发? 答案很明显:西方的开放社会和宪政国家必须将自己与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区分开来。 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的对比是有目共睹的。 用强制性政治措施应对病毒式传播的浪潮与西方的主张不相容。
然而,这是因为当时人们对开放社会的欣赏根深蒂固吗? 或者是因为与共产主义的分离,从而通过一种特别反共的叙事将社会团结在一起,而用强制性政治措施对病毒浪潮做出反应与这种叙事不相容?
从前者的角度来看,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种趋势再次占据上风,将我们带回一个在集体主义叙事下封闭的社会。 因此,让我们换个角度:在1989年以前的开放社会中,有一个以反共为核心的实体叙事塑造了这个社会,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事实。 偶然的不是叙事的存在,而是它是反共的。
因为在特定情况下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叙事必须是反共产主义的,所以它必须允许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和一个基本上是共和的宪政国家。 国家权力的代表不能对内太过压制,不能干涉人民的生活方式。 叙述不允许这样做。 但这仅仅是由于偶然的历史环境。 当敌人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而消失时,这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使这种叙述变得多余。
由于盛行的不是作为开放社会的开放社会,而仅仅是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依赖于允许相对开放的社会为其所服务的社会凝聚力,因此以叙事缺失的形式出现了鸿沟。 然后,在这一差距中推动了一种叙事,虽然表面上将其修辞与现有的开放社会联系起来以征服其制度,但实质上做了本应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叙事——以及推动此类叙事以行使权力的人以公共利益为名的权力——倾向于做:建立一种集体主义,人们必须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服从。
为什么社会凝聚力和集体主义叙事优先于开放社会的原则? 为什么现在出现的集体主义叙事恰恰假定共同利益都包含保护免受某些东西——保护免受病毒、保护免受气候变化、保护免受可能伤害群体感情的意见(即使是真实的)大声(清醒)?
共和宪政国家后来发展为自由民主国家,是开放社会的政治秩序。 法治以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强制每个人尊重其他人的自决权的义务,以保证安全免受对生命、肢体和财产的攻击。
为完成这项任务,国家权力机构被赋予上述两项权力:(i) 在各自领土上的武力垄断(行政权)和(ii)立法和司法权(立法、司法)的垄断。 然而,这种垄断赋予了共和立宪国家机构以早期国家所没有的全部权力。 例如,如果社会在基督教的形式下是封闭的,那么国家机关也受制于这种宗教。 他们立法和执行司法的权力受到这种宗教的限制。 如果国家权力的代表越过这个界限,教会、神父和平信徒都可以合法地反抗。 相比之下,在共和宪政国家,这是不可能的。 矛盾的是,国家权力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无限权力是开放社会价值中立的结果; 即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普遍存在的实质性共同利益学说这一事实的结果。
共和国家的任务是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肢体和财产免受他人的攻击。 这是与武力垄断、立法和管辖权相关的权力的基本原理。 但是国家如何提供这种保护呢? 为了有效保护其领土上的每个人免受他人对生命、肢体和财产的暴力攻击,国家当局必须时刻记录每个人的行踪、监督所有交易等。
然而,这会使宪政国家变成极权主义的监视国家。 法治从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免受他人侵犯的权力转变为本身侵犯其领土上的人的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同样,只有国家当局才能判断这一点。
问题是这样的:一旦有一个国家在一个领土上拥有武力垄断权以及立法权和管辖权,这种权力的持有者往往会以进一步加强对领土的保护为借口扩大他们的权力。其领土内的每个人免受他人侵犯。 换句话说,这种权力的集中恰恰吸引了那些想要行使权力并因此从事国家权力工作人员职业的人——尤其是政治家,他们试图以更广泛的保护承诺赢得选举.
这样,福利国家逐渐出现,它垄断了对各种生活风险(疾病、贫困、老年无法工作等)的保护,从而排挤了本来会提供这种福利的志愿协会。保护。 福利国家通过保护人民免受生命风险,以技术官僚的方式将其领土内的人民与自己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我们已经离开放社会迈出了一大步:一个地区的人民被该地区的国家机关以垄断的方式保护起来。 结果是与其他人的分界。 相应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即19世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th 世纪。 福利国家因此发展为战争国家。
在民族主义崩溃并且反共主义的叙事在西方也变得多余之后,全球主义叙事取而代之,这是全球主义的,也是由于缺乏其他可以区分自己的强大国家(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 ,必须反过来利用所谓的科学来证明其合法性(政治科学主义),并且必须为自己提供更好的生命风险保护形式 - 包括保护免受病毒,气候变化,反对可能伤害直言不讳的人的意见(清醒)。 因此,这种叙事表面上与现有的开放社会联系在一起,但却将其转变为它的对立面,即转变为一个全面的社会控制系统。
福利战争国家只是需要这样的叙述才能继续存在。 这是对自 2020 年春季以来变得明显的发展的解释:这种发展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那些像我一样没有预料到的人,受到了共和主义的幻觉,共和宪政国家的幻觉是保护人民基本权利和实施开放社会的制度。
出去的路
一旦我们认识到共和主义所导致的困境,我们就可以自由地打破开放社会与共和宪政国家之间的联系,只要后者的特点是 (1) 武力垄断和 (2) 权力垄断立法和管辖权。 我们也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点。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普通法是一种寻找和执行法律的方式,它不依赖于中央国家权力机构在一个领土上垄断武力以及立法和司法机构。 这主要是发现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的情况:承认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行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时侵犯了他人自由生活的权利。
与每一种认知情况一样,这种认知最好通过允许试错或纠正的多元化而不是单一权力的垄断来实现。 基于自然法的自由权利可以明确定义为财产权,包括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因此无需中央国家权力机构立法解决冲突即可实施。 同样,国内安全服务可以通过自愿互动和联合来提供和执行,而不需要中央国家垄断使用武力——前提是普通法中的法律秩序得到有效实施。
即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保证正义和内部安全,这仍然没有解决一个中心问题:开放社会的特点是缺乏将社会团结在一起以实现实质性共同利益的集体主义叙事。 开放社会与共和宪政国家的联系触发了国家进一步扩大其保护并将这种扩大嵌入塑造社会的叙事的机制。 仅仅通过法律秩序和安全服务来打破这种联系是不够的,而无需中央国家对武力、立法和管辖权的垄断; 还必须防止破坏开放社会的集体主义叙事反过来填补开放社会价值中立性的缺口。
这意味着开放社会也依赖于对自由和自决的积极叙述。 然而,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它必须在如何——以及通过哪些价值观——来证明这种叙述是合理的方面是开放的。 也就是说,它必须适应多元化的叙述,这些叙述一致同意在社会中实施每个人尊重其他人的自决权的道德义务。
我们还没有实现开放社会,因为开放社会与共和宪政国家之间的联系破坏了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只有在国家垄断权力、立法和管辖权的意义上,才能在没有统治的情况下存在。 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如果我们用积极和建设性的东西来反驳集体主义的叙述,我们就可以创造这样一个与他们本来的人在一起的社会。 在此基础上,我对未来保持乐观。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