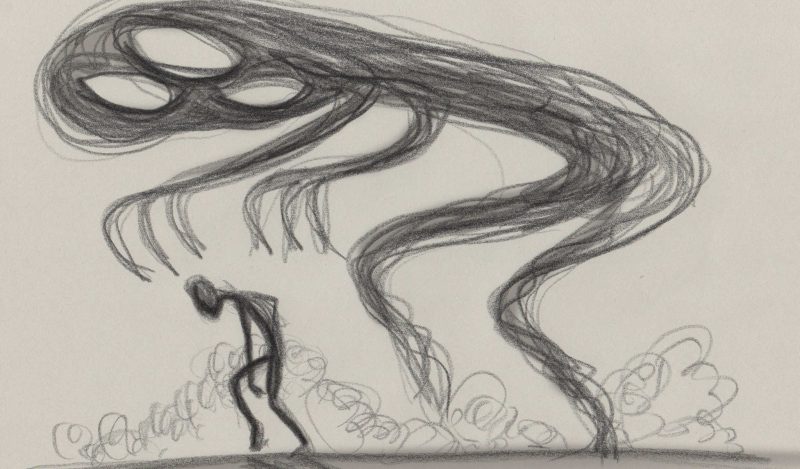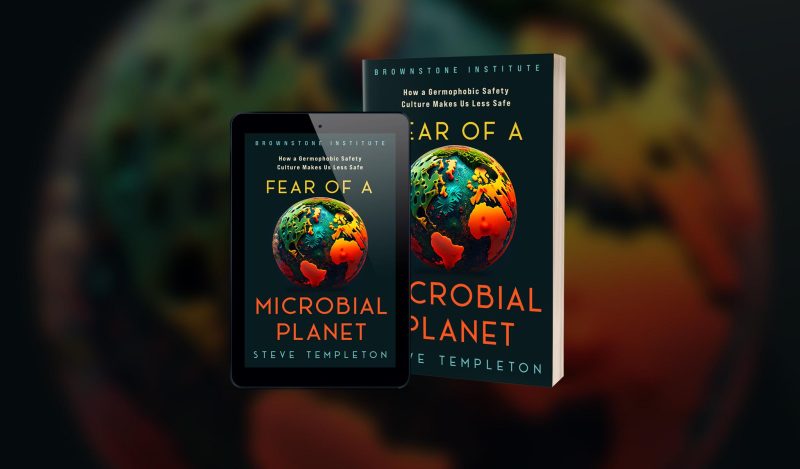作为我的书研究的一部分,将由布朗斯通研究所出版,我最近与社会学家弗兰克弗雷迪博士交谈,他是 恐惧如何运作:21世纪的恐惧文化,关于恐惧文化在 COVID-19 大流行应对中的连续性,以及为什么愚蠢的文化运动几乎总是起源于加利福尼亚。 为清晰和相关而编辑。
ST: 我很高兴你同意和我说话。 我知道你在这里有很多项目,而且你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兴趣。 但我想回去谈谈你的书 恐惧如何运作. 我承认我没有看到很多关于你所说的关于大流行的内容,阅读你的书我意识到那里有很多主题对于如何解释大流行的反应是绝对完美的——你写的关于我们如何看看风险和恐惧。 我想先回过头来谈谈你对研究恐惧定义的兴趣以及你认为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FF:我开始感兴趣——与其说是恐惧——而是围绕恐惧的文化的运作方式,这实际上是英美社会开始看待风险和看待威胁以及趋向于我所说的最坏情况的特定方式- 始终与人类经验的任何维度相关的案例思考。 我对恐惧集中在儿童身上的方式感兴趣,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它们在所使用的语言和问题的框架方式上具有非常相似的模式。 所以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这种特殊的威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且事情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变异为一种生存威胁。 因此,本质上是技术性的问题,几乎立即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甚至在技术上是人类生存的问题。 因此,这基本上意味着,当您遇到大流行病时,就公共卫生变得政治化和政治化变得医疗化而言,叙事已经到位,因为人们已经倾向于认为人类无能为力。处理东西。 我们有一种非常宿命论的反应,在这种恐惧的表现方式中,你基本上围绕病毒的传播重新组织了世界——病毒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系统,等等。 所以我在这一切中看到了一条连续性。
ST:我想我会换个说法,我会说文化环境促成了这一切。 因为任何领导者都希望——他们在想“我要做什么来表明我已经采取了行动,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我已经采取了”——这不一定是决定性的行动,但至少是它的出现——以及“我们将把风险消除到零”。
FF: 这在英国很明显,最初政府对大流行有正确的直觉——你知道他们的反应——他们不会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 然后媒体完全歇斯底里,所以他们基本上支持任何想要封锁的人,向政府施加压力,基本上它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并屈服于这种压力,因为他们害怕如果有人死了,他们会受到指责。 并且害怕他们会变得非常不受欢迎。 如你所知,出现了我所说的封锁生活方式,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人对被隔离而不必外出持积极态度,这真是太棒了。 我不必来教我的学生和其他所有的那种被动反应。
ST:您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所有事情的影响——车祸和任何形式的风险——只要一直呆在家里,在 Zoom 上工作。 我认为其中一些是由于——你在你的书中谈到了这个——人们处理不确定性。 为什么现在的人比以前更不擅长?
FF:不确定性变得可控的方法是将风险转化为可计算的现象,这需要更多的知识——对知识有更大的信心,需要对人类社会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有更大的信心,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而在现代历史上,不确定性也被认为是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 它被认为是为人们提供了走自己的路的机会。 现在它被认为是坏的,完全是负面的。 因此,不确定性变成了这种你想回避、逃避而不是面对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由最坏情况思维的发展所持有的,或者我在书中我称之为可能性思维的东西,即概率——你不能再使用它们了。 您可以假设最坏的情况,即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很可能会出错。 这通过预防原则和环保主义最清楚地表达出来。 我的意思也是健康——整个公共卫生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ST:而且你认为大流行只是加速了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大流行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只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它进入了超高速状态?
FF: 很明显,当事情在大流行期间加速,并且当先前存在的趋势变得加剧时,这可能代表着重大变化,或者至少可以被察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容易谈论新常态的原因。 或者是大重置,因为在他们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革,没有意识到这些趋势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但我认为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是一面镜子,让社会可以看到已经存在的问题,并将一切提升到不同的水平。
ST:为什么人们没有看到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造成附带损害的可能性? 这只是瞬时短期思维与长期思维的问题吗? 显然,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权衡取舍。
FF: 是的,有。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很多人可以看到经济将解体,而你将在全球经济事务的某个层面上发生非常严重的扭曲。 并且对儿童的教育和其他方面有附带损害。 有一种麻痹的感觉,就好像为了限制病毒可能造成的破坏,必须放弃一切,所以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宿命论,命运以高度医学化的形式获得了这种优越感。
ST:不确定性的概念——人们无法处理它——他们试图给自己确定性,即使它只是表面上的。 然后有人愿意挑战这种确定性的幻觉,他们对宿命论持怀疑态度。 但现在怀疑主义是一个坏词。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对于那些对事情的发展方式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如何受到对待的?
FF: 我写了很多关于怀疑论病态化的文章。 你知道气候怀疑论者或在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任何形式的怀疑论——曾经是一种光荣的、知识分子的取向,对科学来说非常重要——只是变成了他们所谓的否认主义并变成了这种准病态你必须揭露并赶出去。 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关闭了辩论和讨论。 但另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开始持怀疑态度,然后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采取阴谋论的解释。 因为他们可以看出事情不对劲,所以他们没有得到事实或真相。 他们有点颠倒过来,一方面你有这个非常讽刺的辩论,但这些人变成了反病毒者,你知道,整件事都是发明,病毒不存在,你有公共卫生大堂,主要是政治阶层的文化,所有的精英都在一边。 因此,很少有理智的人指出不要从属于生活,不要让公共卫生成为一切,这是一次非常徒劳的讨论。
ST:如果你取缔合理的辩论,你就会得到一个不合理的辩论,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仅对阴谋论者使用否认主义这个词,而且对于任何不同意你的人,你都不能进行合理的辩论。
ST: 你的书的另一部分我真的很喜欢你说“研究展示”这个词具有仪式咒语的特征。 你对这个术语有什么看法,以及它在过去两年里是如何使用的?
FF: 但是两年多了一点,就有了这种准宗教的性质——几乎就像“如上帝所说”,而另一个表达方式是“根据证据”。 并且有这样一个假设,即“研究展示”不仅仅是一组事实,而且是关于如何引导你的生活的处方,因此它进入了行为、道德的领域,所有这些事情都由此产生。 它经常被调用,以避免讨论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你想做什么,因为无论“研究表明”什么,重要的是你在特定时间做出了什么决定。 你如何解释它,你如何对它做出反应。 这不是研究表明的,而是通过讨论、辩论和审议产生的。
ST:科学共识的想法已经变得完全不现实——人们很早就要求答案——跳上孤立的预印本研究,当人们并不真正理解科学共识需要数年时间时,你不能说一项特定的研究是确定的建造。 它必须通过一些无私的人来实现,他们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最终会达成某种协议。 我想这已经被扔到窗外了。
ST:我喜欢用“安全的表象”这个词,也有人称之为“大流行剧场”,但我认为政客和他们的决策都是文化的下游。 当人们要求确定性时,它们只是反映了文化是什么——他们必须给他们确定性。 而当他们不能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给他们幻觉。 因为那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满足公众的要求,而这种安全文化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一切的形式。 大学里有些学生的观点无法被质疑,现在我们又绕了一圈,也谈论传染病。
FF: 是的,虽然文化不是从天而降的。 这是利益集团、政治家和所有这些人的成就,对他们来说,这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便捷方式,并且是有趣的——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过去 25 年、30 年里,你如何看到经济的稳步扩张安全所包含的问题,因此安全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概念蠕变的影响,并且它获得了一些动力,这是很多人在推广的同谋。 人们需要被社会化并被教育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思考。 看看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方式,他们的成长方式,以及他们被告知他们是脆弱和无能为力的,我们有特殊需要和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实际上被当作病人而不是患有疾病的人对待独立行为的潜力。 因此,当他们成为年轻男女时,即使在非常安全的环境中,他们也会非常意识到缺乏安全感,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校园安全的想法已经成为这个大问题。 校园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但它就像丛林,你将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ST: 我猜你说的是领导者可以利用这一点——这对他们有利——他们可以表明他们正在做一些可以表明他们正在采取行动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实现,各种各样的永久循环,试图找到更多你可以“安全”的事情。 我们如何摆脱这个循环? 是否会发生任何形式的文化反弹?
FF: 我不认为文化上的反弹会起作用。 反弹从来没有像它所反对的那样强烈。 这是过去 20 或 30 年的问题。 他们真的很生气,他们说够了就够了。 但首先,你需要彻底重新定义人是什么。 其次,我们需要改变抚养孩子和社交的方式,因为我认识的每一代人,越年轻,他们就越厌恶风险。 他们越是受制于并沉浸在这种“安全空间”的前景中。 这与他们的个性无关,只是他们接受教育和社会化的方式,几乎被教育系统变得无能为力。 然后当你上大学时它会进一步加强,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因为你必须挑战所有这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在生命早期发生的地方。 所以,是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人们往往会低估它的广泛性,以及它有多少文化支持。
ST: 这完全引出了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 西方世界是否有某个地方避开了这种文化,设法避免了这种文化,或者至少减少了这种安全、恐惧的文化?
FF: 自从我研究它以来,就我看来,它总是从加利福尼亚开始。
ST:
FF: 说真的,所有这些愚蠢的事情总是从那里开始,然后它们被出口到东海岸,然后美国其他地区受到牵连,然后到加拿大。 六个月后,这些情绪传入英国、英国,最终传入北欧,然后可能在一两年后逐渐传入南欧,并可能传入东欧。 但是有一个时间上的差异,英美世界是最糟糕的,并且其中存在差异。 但问题是,由于美国软实力在全球的作用,它甚至开始影响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所以如果你去上海或孟买,你会发现,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孩子们就像对旧金山环境的拙劣模仿。 它通过 Netflix 传播——所有这些不同的事物和文化模式。
FF: 我在意大利和东欧度过了很长时间。 我每年在意大利呆三个月,在匈牙利呆三个月。 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而且那里更好,很高兴看到更轻松的环境。 但你真的可以看到,即使在那里,它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但美国属于自己的一类。 当我看到美国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时,这令人难以置信。 我在书中提出了这一点,你知道,我在布鲁克林,我正在和一些老朋友聊天,我说,“我要去买瓶酒,”他们说,“留下安全,弗兰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好像走几个街区会对我的存在构成威胁。 正是这种整体意识深刻地将美国人的个性从一种粗犷的个人主义转变为非常非常不同的东西。
ST: 是的,绝对的。 我正在与另一个州的人就我正在处理的一些业务事项进行电话交谈,特别是在大流行期间,人们会以“好的,安全”的方式签字。 那会让我发疯。 而且,我想说的是,“任何可以做的事情都应该做得过火”,这是一个非官方的美国格言。 我认为这是我们擅长的事情,少量可能相当有用的事情,并将其增加到完全适得其反的数量。
ST: 你说的事情从加利福尼亚开始并传播到世界各地。 有什么方法可以量化吗? 这只是您的意见,还是您可以查看 Google Analytics 并找出答案?
FF: 我相信你可以。 我记得当我写一本名为“治疗文化”的书时,你注意到所有关于自尊的胡说八道在加利福尼亚开始流行,我只是注意到经常出现对人际关系主题的担忧。 如果您要列出所有这些不同的新恐慌,我相信您可以解决。 我曾经和一位名叫乔尔·贝斯特的美国研究社会学家做过一个研究项目,我们正在研究这个,一个社会问题的发明。 因为它通常从美国传播到欧洲,唯一不同的是当我研究了欺凌这个概念的发明时。 你在出生之前所拥有的,欺凌过去只是孩子们对彼此所做的。 没有欺凌问题。 然后它变成了孩子们的大问题,然后变成了成年人工作场所的主要问题。 你把所有这些人都幼稚化了。 它始于瑞典和瑞士的工会,基本上是利用工作场所的欺凌作为增加人力资源作用的一种方式,然后它传到美国并很快被接受。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从欧洲开始的事情,其他一切都在另一个方向。
ST: 是的,这真的很有趣。
FF:加利福尼亚的另一个例子是 1980 年代的撒旦虐待歇斯底里。 我想人们可以看很多这样的东西。
ST:所以你认为好莱坞是这方面的主要推动者,因为那是在加利福尼亚吗?
FF:我认为这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直到最近,人们移居加利福尼亚的人数与新成立的人一样高,你知道,人口流动性很大,背井离乡,分散,但我认为一定有什么别的。 也许这是一个文化精英人士更加成熟的领域。
ST: 你提到瑞典很有趣,因为我倾向于认为北欧国家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比欧洲其他国家和盎格鲁圈松懈得多。 我觉得这是他们文化的反映。 他们强调个人责任。 他们没有表现得像他们的孩子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他们让学校保持开放——即使关闭的地方也没有关闭很长时间。 这让我回想起几年前我在丹麦的时候,我在那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我和一位合作者共进晚餐,他提到了一对来自丹麦的夫妇来到美国的例子在纽约一家餐馆吃晚饭时,他们把婴儿放在婴儿车里,然后把婴儿放在人行道上的婴儿车里,这样他就可以看到路过的人。 他们因为在丹麦非常普遍的做法而危及他们的孩子而被捕。 他们仍然对为什么美国人如此痴迷于安全和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感到困惑,尽管统计数据并未证实这一点。 您谈到来自瑞典的欺凌行为,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似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能给我你的想法。
FF: 不,我认为你是对的。 我最喜欢的国家是丹麦。 丹麦的风险厌恶程度要低得多。 挪威在政治上确实是正确的,痴迷于环境。 瑞典位于中间。 芬兰没事。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没问题。 瑞典过去比现在好得多。 尽管我认为情况正在变得更糟,但它显然仍然没有涉及同样的安全文化。 而且您必须记住,瑞典对大流行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人的行为。 首席医疗官不肯翻身,还真挺住了,权势很大。 所以很容易想象在美国,像福奇这样的人会像他一样,他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且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然他确实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在四五个月之后,他也坚持了下来。 好消息是瑞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瑞典有足够多的人支持这一决定,并且拒绝屈服于所有压力。 瑞典从欧洲各地得到的所有批评都令人震惊。
ST: 是的,我觉得瑞典以外的情况比国内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你总能读到关于批评国内事物的人的故事。 但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确实支持没有停课和学校停课。
ST:你是一名社会学家,但你似乎并不持有大多数社会学家的传统观点,因为你更重视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利益,所以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你的工作是如何被你的同行接受的。
FF: 直到最近,还不错。 就学术环境而言,我在英国享有很高的声誉。 最近,它变得更加消极,对我一直在写的东西充满敌意。 世界上有些地方我的作品真的很受欢迎,比如芬兰。 我刚从那里回来,他们刚刚在那里翻译了我的一本书。 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这些地方做得非常好。 但你必须记住,我正在做的事情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因为我也写关于政治的东西,特别是目前我正在做很多关于文化战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方式的东西身份政治、变性主义和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以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用来搞乱孩子,所以我对此很感兴趣。 显然,这在我的同龄人中不是很受欢迎。 但我正在对更广泛的公众产生影响,并且我有一定的追随者。 但问题是,事情是两极分化的,你要么有规避风险、有身份、有安全空间的一面。 然后你有相反的情况,这几乎是漫画,他们对此的反应方式几乎是极端反动的。 真的没有我所谓的老派自由主义对待世界的方法往往相当有限。 如果您可以提供另一种世界观,那么生活在激动人心的时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FF: 比如我 写了一篇文章——有一本杂志叫 社会 在美国——关于社交距离,发展我的想法。 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在同行中也是如此。 所以我的一些书做得很好,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将是一个非常次要的意见。
ST: 所以你已经回答了你的信仰是如何被你的同龄人接受的,但你并没有完全理解“起源故事”,比如你是如何到达你的信仰驱使你进入社会学和你的背景的地步的。
FF:这是一段旅程,因为我在学生时代曾参与过极左派,我真的很享受,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 1980 年代的某个时刻,我意识到左右区分确实没有帮助,而且在很多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大问题不是左派过去争论的问题,而是关于对个人采取立场的问题权利,更加认真地对待宽容和自由的价值观,不假思索——我记得醒来时,我意识到我的观点逐渐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就像我之前接触过的很多左翼人士一样关于——他们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他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或多或少我是那种我称之为“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的人。 我讨厌使用这个标签,因为有些东西我不会自称,比如美国人(自由主义),比如 原因 杂志。 例如,我对市场机制的信心与他们不同,我认为这需要稍作修改。 但在个人事务以及人类行为和与自由相关的问题上,我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 这就是改变我的方向的原因。 我记得我曾经受到左派的谴责,因为在 1970 年代,我是英格兰唯一一位反对那些想要无平台种族主义者或无平台法西斯主义者的大学教授。 我说如果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那就想办法反对他们,而不是找到一种官僚的方法来关闭他们。 那时我意识到我不像他们。
ST:基本上,一旦左派放弃了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坚持,你就离开了?
FF: 非常非常快。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