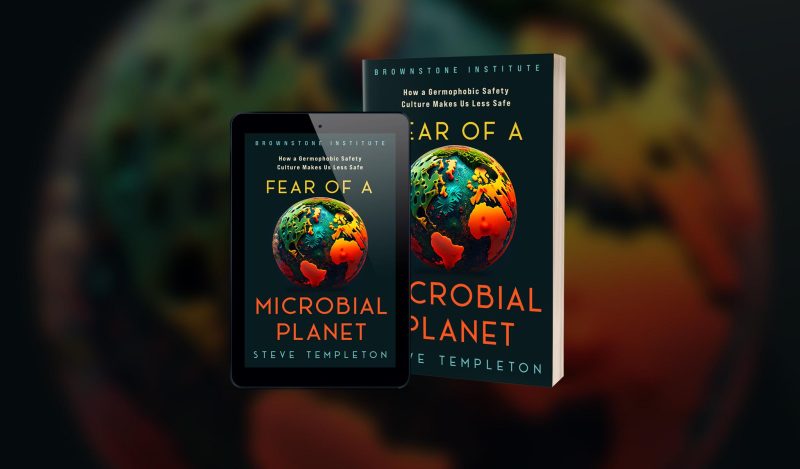在圣诞节前的几周里,中西部家庭主妇玛丽安·基奇(Marian Keech)为世界末日做准备。 一段时间以来,玛丽安一直在尝试自动写作,与超凡脱俗的人交流。 他们告诉她其他星球上的生命。 他们警告她即将到来的战斗、瘟疫和毁灭时刻。 他们承诺开悟和幸福。 玛丽安需要做的就是相信。
尽管家人不太相信玛丽安的预言,但在夏天,玛丽安取得了一些成功,吸引了更多思想开放的人加入她的事业,以及偶尔寻求好奇心的人。 在这些人中,有医生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 Armstrong)博士,他在当地一所大学工作,经营着一小群“寻求者”。 到 21 月,玛丽安·基奇 (Marian Keech) 为她的运动积累了一批温和的使徒,其中一些人冒着教育、职业和名誉的风险,同时为 XNUMX 月 XNUMX 日即将到来的大洪水做准备。
这一年是1954。
不用说,玛丽安和她的追随者耐心等待的灾难性事件从未发生过。 对几乎无法避免的世界末日的一种解释是,玛丽安·基奇和她的一小群追随者通过他们对事业的奉献拯救了世界。 另一个是不知何故他们弄错了日期,而末日仍在到来。 然而,另一种解释是,那些日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到来。
幸运的是,在 21 年 1954 月 XNUMX 日那个决定性的夜晚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件在社会心理学的开创性出版物之一中得到了很好的记录, 当预言失败.
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Leon Festinger 招募了几名研究助理来渗透 Marian Keech 的小组并向他报告,作为一项观察性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研究了当一群对某个信念充满信心和承诺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发现他们的信念已被明确否定。
虽然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值得怀疑, 当预言失败,仍然是一部对新生宗教的兴衰和信仰力量的宝贵洞察力的作品,有时读起来也像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里面充斥着外星漂泊者、伪装的太空人、星际神灵和争吵的媒介,或者至少那些看到所有这些东西的人,即使这些东西从未在那里看到。
结局是开始
将近 70 年后,在前时代的最后几天的一个下午,站在北伊利诺伊大学生物大楼三楼大厅周围,我和一位研究生、一位教授开玩笑说我们无能的州长和阿谀奉承的大学官僚急切地寻求成为第一批执行我们不称职的州长对我们大学的命令的人。
我们嘲笑相互竞争的公共卫生官员如何无法决定我们应该在随意交谈中保持三英尺还是六英尺的距离。 我们惊讶于我们过于热心的管理员可能会开始要求我们通过 Zoom 与大厅里的同事一起参加会议,而我们可以,你知道,只是聚集在会议室或去大厅另一边的同事办公室。
我们是生物学家——或者至少是受训的生物学家。 我们发现如此多的人对流感反应过度是荒谬的,即使在那时,这似乎是一个严重的流感病例,除了非常老或病重的人外,对任何人几乎没有威胁。
然后我们的大学官僚宣布他们将春假延长一周,一旦恢复,课程将暂时转移到网上。 然而,在最后一两周的准常态期间,当我在生物大楼的大厅里闲逛时,我遇到的教授或研究生仍然很少有人对面对面的随意交谈表示任何不安或不适。 没有人测量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 没有人戴口罩——我们中的几个有微背景的人过去实际上曾与潜在的致病真菌或细菌孢子打交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知道,大多数口罩在阻止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方面非常无效。
当我与我的各个主管联系时,我愿意留在现场并在任何情况下继续保持高效,没有人真的太用力了——至少直到我们都或多或少地被禁止州长法令的实验室。
尽管如此,对于社会重组似乎仍然存在一些微妙的怀疑,这似乎超出了我和与我保持联系的一小群朋友,偶尔冒着轻度至中度疾病的风险,并可能激怒福奇老人当我们的学校和州希望我们呆在家里时,冒险出去享受一个面对面的欢乐时光。
直到我们或多或少被允许返回校园后,我才知道我剩下的大多数同龄人和教授已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几个月前我们一直在嘲笑的事情。
不仅是视觉和声音的维度,而且是心灵的维度
我在这么多以前的同事身上看到的大变脸的原因是我最初对此感到困惑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谢 早 工作 斯坦福流行病学家 John Ioannidis 等研究人员认为,Covid 似乎不那么可怕,而不是更可怕。 此外,我们大概都在夏天重温了近 5 年前的经典大流行规划评论,当时 H1NXNUMX 禽流感爆发的可能性严重影响了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的人员。
那个时期的一个又一个报告中设想的情景严格地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种致命的病毒没有疫苗、有限的治疗方法和快速的、有时是无症状的传播困扰世界,政府能做些什么。 当时的共识并不多。
兰德国内和国际健康安全中心的一个小组, 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安全中心的一个团队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以及对 国民 和 国际干预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对封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的支持缺乏证据。
在 H5N1 恐慌和 Covid-19 大流行之间的时期,类似的评估发表在期刊上,例如 流行病 和 新兴传染病 大体上与那些早期大流行规划者的意见一致。 后者实际上是在 2020 年 XNUMX 月问世的。
同样,在讨论模型时,过去的大流行规划者往往同样不屑一顾,将它们降为次要角色,理由是他们的预测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并且无法预见具体措施对人类行为或其下游社会后果的影响。 上述预测的长期准确性还有待认真评估。 什么时候 此类评估 终于做出来了,结果似乎是这样的模型在超过两三周后并没有真正的预测。 在 2020 年 XNUMX 月之前,除了尼尔·弗格森之外,没有人似乎因为他们而过于渴望关闭社会。
当然,我和我的欢乐时光伙伴小圈子并不是唯一一个费心阅读这些文章的人。 我们是生物学家——或者至少是受训的生物学家。 我知道有一个事实,在那栋楼里有人,在时代之前,会吹嘘要花一个周末阅读兽医和微生物学期刊上的成堆文章,以确认他们的兽医为他们的猫开了正确的抗生素。小猫尿路感染。 当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已经费心努力确认我们的政府和大学已经就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政策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但相反,我在这些生物学家和受训生物学家中发现的情况恰恰相反。 相反,我发现对现在支配我们的规则背后的科学缺乏好奇心。 关于感染死亡率、口罩和模型的对话充其量就像 Solomon Asch 实验。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谈话遭到了某种敌意,或者至少对人们可能需要教皇福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会或“科学”所宣布的证据的想法感到屈尊。
在某个时刻之后,每当我踏入校园时,老实说,我有一半的预期是 Rod Serling 会在我们的一个实验室的某个黑白角落里抽烟,并进行叙述。
真正的信徒
然而,除了穿越一个入口到达光与影之间的中间地带之外,我所目睹的第二个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生物学家和正在接受培训的生物学家已经变得像玛丽安·基奇的真正信徒,就像全国许多人一样在我位于伊利诺伊州北部的小角落之外。
从广义上讲,一个人如何关注、感知和学习很大程度上受个人参考框架的影响。 这是在 1940s 和 1950s. 当信息混杂或不确定时,它可以被同化为具有相反观点的人的当前观点,如 经典研究 从 1979 年开始,涉及人们如何处理与死刑威慑作用相关的信息。
此外,无论一般智力、知识或教育程度如何,人们通常都容易受到这些认知缺陷的影响,因此在这里接受培训的生物学家或生物学家可能毫无意义。 更近 研究 甚至已经证明,在科学问题上,如果科学信息与个人的宗教或政治身份相冲突,对科学的一般理解甚至不需要接受科学信息。
不要不必要地政治化,但美国的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科学的拥护者,这在整个布什第二届政府期间似乎是合理的,当时民主党人通常为进化生物学辩护反对神创论并认真对待气候变化(尽管当民主党开始积极否认生物性别的存在时,他们可以说失去了一些科学的街头信誉,因为 黛布拉·苏 和 科林·赖特 可以证明)。
然而,当作为“科学”事实上的傀儡的科学机构和科学家再次开始与他们在流行病政策上的宿敌——这次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领导的老对手——发生冲突时,政治战线已经拉开。在某种程度上,你要么站在民主党和“科学”一边,或者站在共和党和特朗普一边。
从今以后,如果成为民主党人、反特朗普者或相信科学的人是你核心身份的一部分,那么你现在会发现自己处于捍卫“科学”及其所有相关领导人、信仰和政策的位置并在非常核心的层面上这样做。 不管你是否跟随“科学”进入了心理的暮光区,对科学的承诺的特点不是批判性思维和对数据和证据的仔细评估,而是服从权威和捍卫一个象征性的表征。机构。
因此,我认识的许多曾经看似通情达理的生物学家和接受过培训的生物学家都表现出极度缺乏好奇心,或者对有人可能需要为教皇福奇所宣布的证据提供证据的建议表示敌意和屈尊俯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堂,或“科学”。 对一些人来说,质疑“科学”所宣称的东西就像质疑玛丽安·基奇所揭示的东西一样。
媒体中的医生和评论员(如 1954 年的业余不明飞行物观察者)为各种流行病学模型的长期世界末日预测辩护,即使其中一些模型虽然没有被明确反驳,但被证明 表现相当差 在他们对诸如 Covid-19 的每日死亡人数和 ICU 床位利用率的预测中。
随着我们现在进入大流行时代的第三年,真正的信徒继续认为,那些“追随科学”的人通过他们的行为拯救了世界,无论这些行为最终被证明是多么具有破坏性。
而且,即使在“科学”预言的最具灾难性的事件没有发生之后,仍然有一群真正的信徒核心相信“科学”只是弄错了日期或变体,并且认为世界末日除非我们都保持警惕,当“科学”说是时候了,永远准备好掩饰和封锁。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