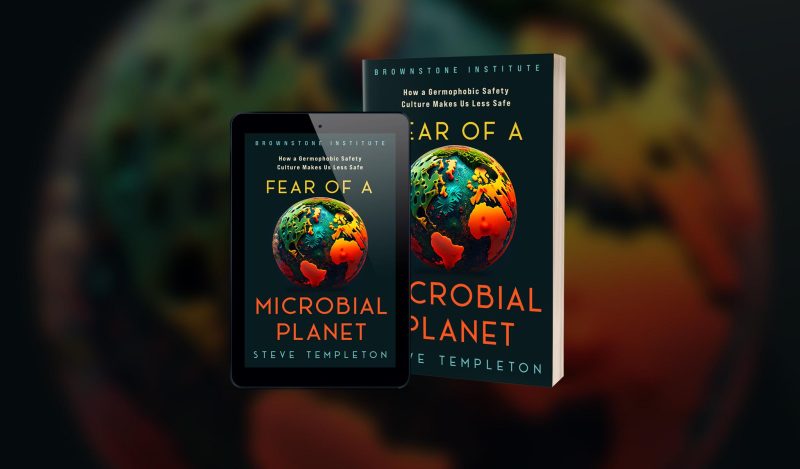的推力 让百花绽放 是世界对 COVID-19 的反应不应该被排除在政策形成和发展的正常过程之外,在民主国家中,这些过程的核心是辩论。 通过免除大流行病政策的批评,各国政府试图确保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但实际上增加了陷入严重错误的可能性。
各国政府认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没有时间探索替代政策,必须采取纪律严明的方法来击败敌人(即病毒)。 政府有必要控制中央向民众提供的信息,并压制可能传播“不正确”信息的“不可靠”信息来源,从而导致误入歧途的人们死亡。
众所周知,新西兰前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宣称“我们将继续成为您唯一的真相来源”。 她建议新西兰人民听取卫生总干事和卫生部的意见,“不要理会其他任何事情”。
不应该出现政府和政府机构是唯一真相来源的情况。 任何组织、个人和个人团体都不可能是绝对可靠的。 她现在正前往哈佛大学,与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一起阐述虚假信息。
因此,我们需要首先经历一个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在这个阶段咨询所有相关的不同知识来源和不同的声音。 这有时被称为“群体的智慧”,但“群体的智慧”必须与“群体的群体思维”区分开来。
股票市场上公司的价格被认为反映了所有交易者的综合知识,因此反映了真实的市场价格。 但股票价格会经历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其中真正的基础价格被著名的“动物精神”扭曲了一段时间,并在下跌之前呈指数上涨,这确实很像流行病曲线。
需要让不同的观点来解决共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议会和代表大会而不是独裁统治。 人们对议会普遍感到失望,但它们体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著名格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所有其他已经尝试过的政府形式。” 听取所有声音的审慎决策是一项基本保障,如果谨慎部署,可以形成合理的政策,避免集体思维的陷阱,它优于所有其他已尝试过的决策形式。
政府必须选择前进的道路,他们必须做出战略选择,但他们应该在充分了解政策选择的情况下这样做,而且他们永远不应试图阻止讨论其他选择。 但这就是在 COVID-19 大流行中发生的事情。
它是由一种简单化的科学观驱动的,在这种观点中,科学界应该根据针对全体人口的普遍措施,就应对大流行病的最佳方法形成“科学共识”。 但是 大巴灵顿宣言 相反,它提倡“集中保护”的替代策略,最初由 46 位杰出专家签署,其中包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随后,超过 16,000 名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家以及近 50,000 名医生签署了该协议。 无论您如何看待《伟大的巴灵顿宣言》,这些简单的事实表明并没有达成共识。
当活动家提到“科学共识”时,他们指的是“既定共识”——Jacinda Ardern 提到的那种圣贤共识,在“让百花盛开”中提到。 这些机构负责人、顾问小组和卫生部自然倾向于接受他们自己的建议而忽略反对意见。 然而,相反的声音提醒我们“不便的事实”,即与既定观点相冲突的数据。 正是通过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我们才更接近真相。 即使在大流行期间,“当局”也必须承担责任。
建立共识的关键在于它总是完全没有个人洞察力。 为了有资格成为圣人或贤人,并成为政府顾问小组的一员或成为机构负责人,您必须始终表现出遵守纪律的能力,并且从不说任何有争议的话。 乔治·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对此表达得很好:“理性的人适应世界; 不讲道理的人坚持要让世界适应他自己。 因此,所有进步都取决于不合理的人。
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一直由理性的人主导,他们顺风顺水并接受当前的框架,无论它是什么。
2020 年初,在几周内围绕通过封锁抑制大流行病蔓延的大战略(请记住,这既不是大战略也不是战略战略)形成了共识,直到疫苗接种可以结束它。 在那个阶段,没有疫苗存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封锁可以“阻止传播”,但从未考虑过替代策略。 从那以后,当权派在压制辩论方面比在抑制病毒传播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玛丽安娜·德马西 (Maryanne Demasi) 有一种致命的独立思考倾向,这在过去曾让她陷入困境,她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种“审查共识” 子栈文章:“当你压制不同的声音时,达成科学共识并不难。” 诺曼·芬顿 (Norman Fenton) 和马丁·尼尔 (Martin Neill) 等科学家以他们的名义发表了数百篇文章,但如果他们对 COVID-19 疫苗有有利发现的论文提出任何问题,他们就无法发表论文。 他们写下了他们的经历 Lancet 点击此处. Eyal Shahar 举了三个例子 点击此处.
这是无法接受的。 与任何其他治疗产品一样,COVID-19 疫苗应接受严格的持续安全分析,并且必须根据新出现的知识在必要时调整策略。 同样,没有任何例外。
即使有这些障碍,一些论文还是漏网之鱼,例如 Joseph Fraiman、Peter Doshi 等人对主要临床试验证据的严格分析: “在成人随机试验中接种 mRNA COVID-19 疫苗后引起特别关注的严重不良事件。 但是很多关于疫苗有不良发现的论文在预印阶段就被屏蔽了,比如关于 COVID 疫苗接种和按年龄分层的全因死亡风险 Pantazatos 和 Seligmann 得出的结论是,数据表明“COVID 疫苗和加强剂的风险超过了职业风险较低或以前接触过冠状病毒的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益处。”
Pantazatos 描述了他在医学期刊上的经历 点击此处. 这表明,对付逆向研究最有效的策略不是反驳它,而是打压它然后忽视它。 事实上,机构研究人员忽略了整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COVID-19 疫苗对全因死亡率的影响。 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应对大流行病的整个目标应该是降低死亡率。 但在大规模疫苗接种开始两年后,研究人员还没有对其对总体死亡率的影响进行对照研究,甚至没有进行回顾性研究。 这是不可理解的。 他们害怕他们可能会发现什么吗?
德马西的博客受到了极端正统派大卫戈尔斯基的攻击,后者写道:“Antivaxxers 将科学共识视为“人造结构”。 这个标题是一个很大的赠品——什么时候“antivaxxer”是一个科学术语? 他的博客只是向 Demasi 泼脏水,没有参与她关于流行病政策的争论,更不用说参与她与 Peter Gøtzsche 合写的预印本中的分析了:'COVID-19 疫苗的严重危害:系统评价。
戈尔斯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贡献。 他最接近争论的是个别研究不一定会使科学共识无效。 但 Gøtzsche 和 Demasi 的论文是基于对 18 项系统评价、14 项随机试验和 34 项其他有对照组的研究的元评价。 它已在预印本网站上开放审查,我不知道对其中的信息和分析有任何实质性反对意见。
“anti-vaxxer”、“anti-science”和“cranks”等词是思想障碍——修辞手段旨在向正统派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珍视的信念是安全的,他们不需要理解论点和证据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按照定义是声名狼藉的人,会误导人。 诉诸这些手段和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反智的,
虚假的共识确实是“制造出来的”。 关于 COVID-19 的科学辩论从一开始就结束了,尤其是在意见层面,而真正的科学共识的标志是开放性。
作为一个案例研究,考虑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和“稳态”理论的倡导者之间的大辩论,其历史与 此帐户 由美国物理研究所提供。 稳态理论(宇宙以稳定的速度膨胀,物质不断产生以填充恒星和星系移动时产生的空间)是由他那一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提倡的,超过超过 20 年,直到射电天文学经验观测的重量导致其消亡。 辩论以传统方式结束,稳态理论的预测被证伪。
COVID-19 大流行应对的宏伟战略本应结束大流行并结束过量死亡,但与经验观察相矛盾。 大流行并没有结束,几乎每个人都被感染,大量死亡仍在继续,并且没有确凿的证据,特别是来自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表明疫苗可以预防或降低全因死亡率。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超额死亡发生在大规模疫苗接种期间。
然而,正统派继续对战略抱有信心,并继续忽视和压制替代战略,认为科学已经解决,但似乎显然还没有解决。
这导致了反对“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战争,这实际上是一场反对逆向观点的战争。 政府与权威科学家和社交媒体公司勾结,系统地审查替代观察和策略。
通常用来证明这一点的稻草人论点突出了不合理的想法,例如疫苗含有微芯片的谣言等。但他们完全忽视了 Doshi、Fenton 和 Gøtzsche 等严肃科学家提出的问题。 正统派认为怀疑论者是科学否定论者,而事实恰恰相反:当权派否认科学文献中发现的多样性。
思想市场应该是所有市场中最自由的,因为参与所有源自基于证据的分析的思想可以获益良多,损失也很小。 相比之下,流行病政策的特点是一种知识保护主义,其中正统思想享有特权。
虚假共识已被用作“虚假信息”学术研究的基础。 虚假信息的概念没有精确的概念基础,它被假定为“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谁来判断什么是假的? 这通常被衍生地定义为任何与既定叙述相反的信息。
自封的阿斯彭委员会在其 关于“信息混乱”的最终报告, 提到其中一些问题,例如询问“谁来确定错误和虚假信息?” 并承认“伴随着压制善意异议的风险”——然后开始忽视它们。 没有对其进行定义,关键建议是:“建立一个全面的战略方法来打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传播,包括一个集中的国家响应战略”(第 30 页)。
进一步的建议是:“呼吁社区、企业、专业和政治领导人推广新规范,在他们的社区和网络中为那些故意违反公众信任并利用他们的特权伤害公众的个人造成个人和专业后果。” 换句话说,追捕和迫害那些出格的人,而不考虑他们是否仅仅依靠 不同 信息,不 管理信息系统信息。
- 他们继续就如何实施措辞含糊的建议提出有用的实用建议:
- 要求医学协会等专业标准机构追究其成员与公众分享虚假健康信息以牟利的责任。
- 鼓励广告商停止向其做法未能保护其客户免受有害错误信息侵害的平台投放广告。
- 鼓励媒体组织采用突出基于事实的信息的做法,并确保它们为读者提供背景信息,包括公职人员何时向公众撒谎。
所有这一切都假设在“真”和“假”信息之间存在简单的区别,而在此基础上,天真地相信只有卫生当局才依赖“基于事实的信息”,而相反的观点是自以为是的显然没有事实依据。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Doshi、Fenton、Gøtzsche 和 Demasi 发表了非常基于事实的反向论文。
在人身攻击的学术延伸中,甚至有对持不同政见者心理特征的研究,这让人想起苏联最严重的过激行为。 ChatGPT 提供的关于错误信息的一般研究的例子表明,我们这些质疑既定叙述的人显然被确认偏见误入歧途,“认知能力低下”,并且受到我们的政治观点的偏见。 这意味着那些支持传统立场的人是公正的、聪明的,并且从不被他们的政治倾向所影响。 也许这些假设也应该通过研究来检验?
关于 COVID-19,事实证明,我们持不同政见者也容易出现“认知上的恶习,例如对真相漠不关心或[我们的]信仰结构僵化”,根据 迈耶等人. 这是基于测试人们是否愿意相信 12 个明显荒谬的说法,例如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在你的饭菜中加入胡椒粉可以预防 COVID-19”。 同意这些陈述的意愿被延伸到等同于更严重的问题:
接受 COVID-19 错误信息的人可能更有可能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并向他人传播错误信息。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可能会被相当一部分人拒绝,因为他们被有关疫苗安全性或有效性的错误信息所误导。
这些问题都没有在研究中得到检验,但它被扩展到调查结果之外来证明这些结论的合理性。
在 2020 年哈佛肯尼迪学院错误信息评论的一篇文章中,Uscinski 等人问道: 为什么人们相信 COVID-19 阴谋论? 他们总结了他们的发现:
- 我们使用 17 年 19 月 2020 日至 2,023 日对美国成年人进行的代表性调查(n=19),研究了关于 COVID-XNUMX 的两种阴谋论的普遍性和相关性。
- 29% 的受访者同意 COVID-19 的威胁被夸大以损害特朗普总统; 31% 的人同意该病毒是有意制造和传播的。
这些信念当然值得商榷,并被认为再次建立在否认主义的基础上:“一种拒绝专家信息和重大事件叙述的心理倾向。” 否认主义进一步细分为:
- 我们收到的很多信息都是错误的。
- 我经常不同意关于世界的传统观点。
- 政府对事件的官方描述不可信任。
- 重大事件并不总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你是在告诉我这些说法不是真的吗?! 我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一切!
这些研究都将异议观点等同于“阴谋论”。 他们认为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显然与科学记录背道而驰,无效且完全错误; 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参考来支持这一点。 他们高人一等,傲慢自大,对自己不可证伪的学术发现充满信心。
科学方法包含许多有价值的工具来抵消确认偏差——我们都必须将所有数据解释为有利于我们先前存在的想法的倾向。 大流行病科学表明,这些工具本身可能被滥用来强化确认偏差。 这导致了一种客观性陷阱——圣人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免疫的。
他们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持不同政见者必须从根本上反社会,因为他们是“反科学”。 他们要么是坏演员,要么容易上当受骗和被误导。 这些作者没有考虑可能与持不同政见者信念相关的积极属性:独立思考的倾向和本应由高等教育灌输的批判性思维。
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机构一直在努力镇压叛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 但是每个社会都需要(非暴力的)反抗者来挑战没有充分根据的信念。
关于 COVID-19 的既定共识是建立在沙子上的,应该受到挑战。 它源于科学辩论的过早结束,随后抑制了基于证据的逆向分析。 持不同政见者包括科学家,他们显然不是反科学,但反对基于“低认知能力”和支持既定思想的确认偏见的有缺陷的科学。 他们正在推动 更好 科学。
最可靠的政策来自开放的科学和公开的辩论,而不是来自保护主义和封闭的科学。
让百家争鸣——否则我们都迷路了!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