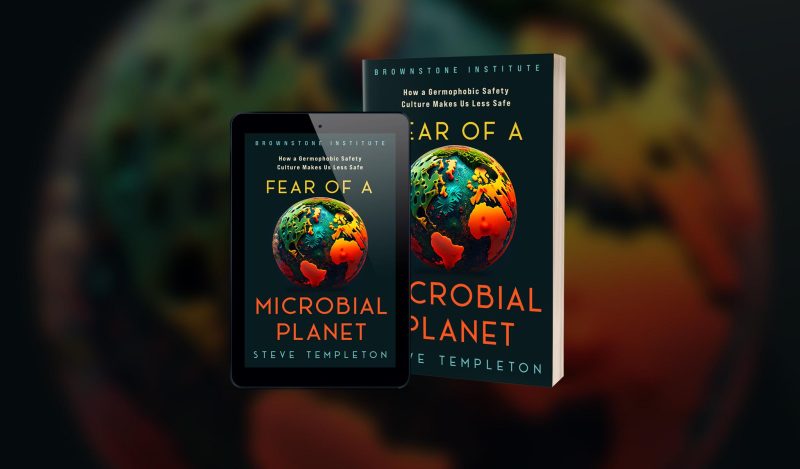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团体增强了我的幸福感——教堂服务、歌唱团体、妇女团体、写作课、书籍讨论、鼓圈、支持团体。 在特别艰难的时候,我在周日参加了两次宗教仪式——早上我心爱的贵格会,经常和我两个长大的孩子一起参加,然后是周日晚上 5 点 30 分的圣公会仪式和圣餐。
一个人总是可以出现在教堂里,也许是在星期三晚上或星期天早上或晚上。 2020 年 XNUMX 月中旬,一切突然以完全停工告终,仿佛一场僵尸大灾难降临了,正如我从儿子们青春期读过的书中所想象的那样。
我没有有线电视,所以我没有收到源源不断的消息,但我有互联网和 Facebook,我的伴侣,现在是丈夫,有有线电视,所以我偶尔会看到这些消息。 电视评论员说,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以防止致命疾病的传播。 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止医院“不堪重负”。 然而,在我家街对面的中型急诊室,两年半以来,停车场里的汽车从未超过四到十辆。 学校停课,学生和老师被送回家。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我预计我们会在我们周围看到更多明显的悲剧——例如,一个近邻失去了两个家庭成员的消息,其中包括他们的主要养家糊口者,他们需要人们带来食物、帮助乘车和照顾孩子. 我们可能收到了来自教会牧师的电子邮件,说有几名教会成员突然死于新冠肺炎,需要吃饭、花钱、探访和庭院工作。
我通常都在这样的名单上,并且通常会报名提供帮助。 我们可能已经接到全县多个家庭成员或朋友的电话,报告说有亲属死于 Covid。 当我通过国际救援委员会 (IRC) 与生活在美国的伊拉克难民一起工作时,我的伊拉克新朋友失去了她的丈夫和她成功的生意。 她告诉我,在伊拉克人中,她认识的每个家庭都在战争中失去了至少一个人。 死亡无处不在,就在他们身边。 他们不必检查电视看它是否在那里。
如果这场危机是“一场战争”,正如政客和官僚在他们的讲台上告诉我们的那样,这场战争需要关闭我们的整个社会,将受惊的孩子隔离在家里,远离他们的学校、朋友和大家庭,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在街上看到尸体,红灯闪烁? 为什么我们整晚都没有听到警笛声? 为什么我在全县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家人 - 或者我丈夫的朋友和家人没有打电话给我们说亲戚死了? 要求我们帮助埋葬死者? 多年来,我有很多朋友和熟人。 我老公也是。
我和我的邻居在我们的院子里聊天。 她不得不关闭她的生意。 我问她是否知道有人拥有“它”。 她说,她听说退休社区的某个人认识某个拥有“它”的人,他们不得不“隔离”。 我的母亲现在住在我附近,她非常参与当地的老年中心,该中心拥有大量会员。 我问她是否认识新冠病毒感染者或死于新冠病毒的人。 不,她说,幸运的是,她不认识任何人。 不过,她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家疗养院的姐姐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或没有。
我知道人们死于这种疾病,当然,我们哀悼所有的死亡。 我根本没有看到我周围的“战争”,正如它所描绘的那样,是政府强制关闭所有人类社区的理由。 我记得弗吉尼亚州的 2020 年春天比大多数时候都更加辉煌,新鲜丰富的更锐利、更多样化的绿色和可爱柔和的色彩,清澈晴朗的天空和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错过了我的会议和我的教堂。 对于上瘾的朋友和亲人,我知道 12 步会议的团契是一条生命线。 团体和教堂是我的; 大多数人没有见面。
我在复活节期间的一个星期天开车兜风,想着肯定有些教堂仍然开放。 也许我现在可以去一些我想去但没有去的地方,因为我不想错过我的朋友和我喜欢的服务。 卫理公会? 黑暗,空荡荡的停车场。 我家附近的浸信会教堂? 空的。 历史悠久的圣公会教堂的旧石楼? 空的。
我在网上看到,12 步会议也不是面对面会议。 仅在缩放上。 通常每周都会在全城举行几次会议。 多年来,我参加了在各个教堂为吸毒者和酗酒者的家人和朋友举办的 12 步会议。 在我的整个成年生活中,在我生活过的所有城市中,瘾君子和酗酒者及其家人每天都可以参加会议,如果他们需要的话,有时甚至一天不止一次。 全部关闭。 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难关? 它何时以及如何结束?
2020年冬天,一位朋友告诉我,每天中午在附近的公园里举行AA会议。 渴望团体团契,我开车去那里开会几次,和他们一起坐在寒冷中。 虽然我不是酒鬼,但我很感激他们在那里,穿着外套,戴着帽子和围巾。
由于健康问题,我无法长时间戴口罩。 在整个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人们宣称没有任何健康状况导致无法戴口罩或戴口罩不健康。 那些在袭击中被窒息或被强行遮住脸的人的 PTSD 怎么办? 还是那些从创伤中幸存下来但通过阅读面孔为自己建立安全感的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那些学习和导航世界依赖于阅读面孔的自闭症儿童或成人呢?
焦虑或恐慌症可能会因缺氧或无法阅读面部线索而危险地恶化,该怎么办? 当人们无法自由呼吸或长期佩戴口罩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周边视力时,感觉障碍或行动问题会加剧吗? 我们对差异和挑战的同情心和敏感性发生了什么变化?
尽管大多数主流教会在 2020 年夏、秋、冬和 2021 年都关闭了,但外来的教会——以及外来的人——支撑着我。 他们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地下教会。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发现离我家不远的乡村教堂,并给牧师和他的妻子发了电子邮件。
他们正在开会; 我不必戴口罩。 他们甚至在周三晚上进行圣经学习,在那里我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坐下来,所有人都没有戴面具,听着关于圣经故事和主题的谈话,这些故事和主题支撑了人们几个世纪——关于怜悯和毅力的故事,关于在可怕的时代保持希望的故事,当这样的希望似乎是不可能的; 穿越黑暗的奇迹故事。
牧师大声而热情,人群中的成员摇晃着,举起手,有时还喊叫着。 我不觉得我必须做任何事情。 人们很友善,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我经常在礼拜期间略读或阅读诗篇——或者只是在牧师的话席卷我的时候把我的手掌翻过几页。 牧师和他的妻子唱着古代和现代的福音歌曲。 舞台上是一幅深邃的耶稣的大画,张开的手伸出来。 我听牧师的妻子唱:“主必使这试炼成为祝福,虽然它把我带到我的膝盖上。” 我以前从未听过这首歌。
一群孩子,他们和家人的长期参加者,有时会唱歌。 一位非裔美国祖母和她的孙子坐在一起。 前排一位可爱的女士在服务期间跳舞和唱歌,然后拥抱了我。 在 2021 年的一场车祸中,我因有人打我而骨折,头部和颈部受伤,我不得不戴上几个月的颈部和身体支架。 住院几天后,在家里康复期间,我丈夫有时会在我不能开车的时候开车送我们去那个教堂。
几年前,在我上班的路上,我被一个乡村门诺派教堂的标志驱车,并想参观。 2020年一个下雪的冬日午后,我开车在山脚下的小溪边的树林里找到了它。 我给牧师发了电子邮件,自我介绍,并要求拜访。 我说我的健康状况使我很难或不可能戴口罩。 他说会众在大型社交大厅而不是圣所开会,所以我不必戴口罩。 几个星期天后,我和丈夫受到了牧师和保守的门诺派社区的热烈欢迎。
几个月以来,我看到了大部分被遮住的脸,他们全开的脸的温暖和光芒几乎让我哭了。 老人、中年人、带着婴儿和孩子的年轻家庭都聚集在一个有折叠椅的大房间里,仍然很近。 孩子们背诵他们背诵的圣经经文。 年轻人第一次传道。 歌声,无伴奏合唱四声部和声,是那样美妙,令人心旷神怡的声音。
快活的牧师问起我的伤势。 他和我们聊了聊他读到的关于伊维菌素的内容。 他和他的妻子请我们吃午饭。 他说,社区的一些年长成员很早就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也感染了,但现在每个人都很好。 那年冬天和 2021 年春天和夏天,我们去过几次。当会众在某人的农场而不是在教堂大楼开聚餐时,牧师提前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有一张地图,所以我们会知道去哪儿。
后来,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门诺派农民到我们这里买牛。 我们谈论了音乐和面具,这一次我们忍受了。 我说我错过了集体唱歌。 他问我是否读过安娜·詹兹(Anna Jansz)的故事,她是一位再洗礼派的殉道者,她的歌声认出她并被杀。 “你怎么能戴着面具唱歌?” 他问。
关闭和封锁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当时所有媒体的头条新闻都在尖叫着任何大小教堂无视命令开会,合唱团无视命令唱歌,然后更多的头条新闻和故事随之而来用一种几乎听起来像欢乐的怪诞声调尖叫着,大概是由于教堂聚会,“病例”成倍增加,有人最终用上了呼吸机,有人死了。 我想知道记者如何能够追踪到这一点。 NPR 采访了一位悔改的牧师,让他说:“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见面。” 这一切都很奇怪。
在 Facebook 上,我看到作家和教师,在大学里工作不错,张贴他们拍摄的学生聚集在院子里,喝啤酒的照片,就像普通大学生一样。 随之而来的是关于这些年轻人如何“鲁莽”和“会让人被杀”,甚至可能应该生病和死去作为对“让我们所有人处于危险之中”的惩罚的可怕和仇恨评论。
然而,外来的教会、团体和人仍在帮助我坚持下去。 遗憾的是,虽然我的 12 步小组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聚会,但由一位亲爱的朋友创立的为吸毒者和酗酒者的家人和朋友而设的小组仍然每周聚会。 它是我们许多人的生命线。 创始人甚至带着桃子皮匠与纸盘一起分享,庆祝集团的周年纪念。 有些人开车长途跋涉到达那里。
以前,我们是在教堂里见面的,但由于教堂内禁止团体聚集,我们在外面的教堂草坪上的树下见面。 如果下雨,我们会在门廊覆盖下见面。 这位朋友 2020 年夏天在她家野餐。当她请人时,她说:“你可以戴口罩,但我和我丈夫不会戴口罩。” 感觉很棒也很正常。 她的丈夫抽肉; 我们都带了小菜。 主流教会,当他们在关闭一年或更长时间后再次开始聚会时,“疏远”了成员,他们遮住了脸,他们不分享食物。
多年来,我参加了一个原声音乐团体,歌手和吉他手在朋友的客厅里相遇。 这是我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它增强了我的健康,振奋了我的精神,我一直很喜欢见到我的朋友。 每个月的一个周日下午,我们轮流领唱歌曲,这些年来我们学到了很多——福音、灵歌、现代歌曲、民歌、抗议歌曲、和平歌曲、摇篮曲、轮播。
我带孩子们在他们小的时候参加了小组,他们在院子里玩耍,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听着,有时也唱歌。 在 2020 年春天结束并且从未恢复。 不过,在过去的两年半中,一个分离小组确实每周都在举行会议。 他们在一座教堂建筑相遇,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这种持续的会面、唱歌和演奏乐器对我来说是一种必要且持不同政见的行为。
自 1930 年代以来,我参加了多年的心爱的教会会议,每年夏天都会举行,但仅在 Zoom 上举行了两年。 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仅限于电脑屏幕的快乐和神圣的聚会。 以前,在这个大会上,每天中午都有一大群人唱歌,下午,各种小团体聚在一起唱——形音、圣轮和圣歌、赞美诗、民歌。 歌手和音乐家也在每晚 9 点左右见面,在睡前唱几个小时。
有课堂、小组讨论、演讲者、鼓手或弦乐合奏的即兴表演。 在一个大食堂里共享餐点,你可以与各个年龄段的普通人,以及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作家、教师和活动家交谈,只需放下你的托盘并询问加入他们。 每个人都很欢迎。 它真的感觉就像上帝在地球上的国度。 然而,在 2022 年夏天,第三个夏天,这个会议只在 Zoom 上举行。
拉格玛芬教堂仍然存在,包括我现在居住的农场附近的一座小型五旬节圣洁教堂。 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参加并演唱了古老的福音歌曲。 没有人戴口罩。 这群人并没有假装Covid不存在; 患有新冠肺炎的人经常在祈祷名单上。 但他们不断地见面,微笑,互相问候,握手。
我还在蓝岭山脚下发现了一座自称为圣经圣洁教堂的教堂,我以前可能没有去过,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一个访客,一个局外人,甚至更多所以比平时。 在 2020 年的几个月里,我每天都必须开车去学校大楼,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教孩子们使用 Zoom。 我在这个教堂看到了星期四晚上礼拜的路边标志,所以我决定在长途开车回家的路上停下来,试图减轻我日益加深的悲伤和困惑,并为我的家人、我的学生和我们所有人祈祷。
门厅干净洁白,鲜花盛开。 我的一些学术朋友可能觉得这位牧师的喊叫、流汗和热情的呼唤很奇怪。 但有时,这个地方让我感到安慰。 我总是受到甜蜜的欢迎,并尽可能多地交谈。 牧师的妻子弹钢琴,带领唱福音。 人们经常去祭坛祈祷,有时还会哭泣。 人们互相按手。 没有隐藏的面孔。
在主流媒体的眩光和噪音之外,更大的教堂也继续开会。 在这个悲伤的时代,为什么没有这些教会的人类兴趣或新闻故事,以不同的声音和经历为特色? 一位亲爱的朋友和她的丈夫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浸信会教堂,该教堂在过去两年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聚会。
我以前可能没有去过,但在停工期间,我很喜欢这个装有空调的大型圣所,里面挤满了各个年龄段的人,他们穿着周日的衣服,唱歌、祈祷、倾听、微笑,他们的脸庞一览无余。 在复活节,当大多数主流教堂都要求在室内戴口罩、“保持距离”并且不分享食物时,大群人欢聚一堂,欢聚一堂。
我不确定我们将如何从这个可怕而陌生的时期中找到自己的道路,充满了混乱和分裂,伤害和损失,但也许分享我们的经历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增长力量和智慧。 我感谢许多局外人,他们拯救了我的心脏和健康,并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期继续这样做。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