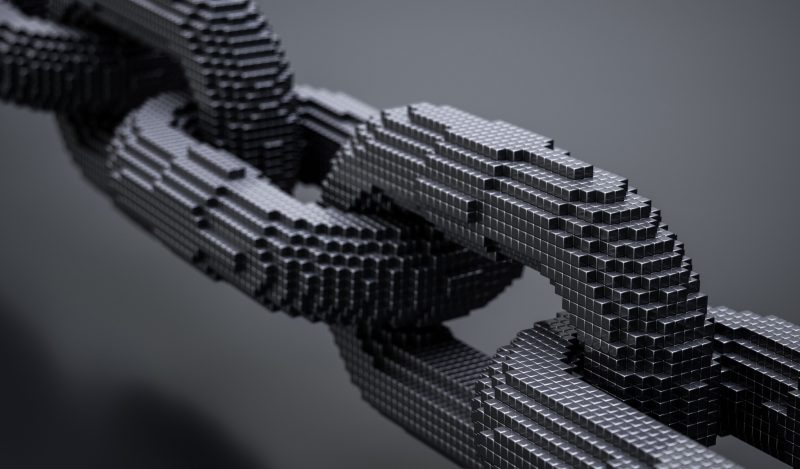1998电影 国家公敌 由 Gene Hackman 和 Will Smith 主演的电影在当时看起来像是虚构的。 为什么我不认为那部电影——它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成立——是一个我不知道的警告。 它拉开了国家安全机构与通信行业之间密切工作关系的帷幕——间谍、审查、勒索等等。 今天,它似乎不仅仅是一个警告,而是对现实的描述。
科技巨头——尤其是数字通信行业——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已毫无疑问。 我们需要辩论的唯一问题是,这两个部门中的哪一个在推动隐私、言论自由和一般自由的丧失方面更具决定性。
不仅如此:多年来,我参与了许多辩论,总是站在技术一边,而不是那些警告即将到来的危险的人。 我是一个信徒,一个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看不出这会走向何方。
封锁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不仅仅是因为如此迅速地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不合情理的严厉政策。 所有顶级科技公司都立即加入了反对结社自由的战争,这加剧了这种震惊。 为什么? 行业意识形态的某种结合,30 多年来从创始的自由主义精神转变为技术暴政的主要力量,加上行业自身利益(促进数字媒体消费比强迫一半劳动力呆在家里更好吗?)在工作。
就我个人而言,这感觉像是最深刻的背叛。 仅在 12 年前,我还在庆祝 Jetsons 世界的曙光,并对我们中间拒绝接受并购买和依赖所有最新小玩意儿的 Luddites 表示鄙视。 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如此美妙的工具竟然会被权力接管并用作社会和经济控制的手段。 互联网的整个想法是推翻旧的强加和控制秩序! 在我看来,互联网是无政府状态的,因此对所有垄断它的企图都有一些内在的抵抗力。
然而,我们在这里。 就在这个周末, “纽约时报” 包含 可怕的故事 关于一位加州技术专业人士,他应要求向医生办公室发了一张他儿子感染的照片,需要脱掉衣服,然后发现自己没有电子邮件、文件,甚至没有电话号码。 一个算法做出了决定。 谷歌尚未承认有不当行为。 这是一个故事,但却象征着影响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巨大威胁。
亚马逊服务器仅保留给政治顺从者,而 Twitter 在 CDC/NIH 的明确要求下进行的审查是大量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可以而且确实会包庇任何不合常规的人,YouTube 也是如此。 这些公司构成了所有互联网流量的大部分。 至于逃跑,任何真正的私人电子邮件都无法在美国注册,而我们曾经的朋友智能手机现在作为历史上最可靠的公民监控工具运行。
回想起来,这很明显会发生,因为历史上所有其他技术都发生过这种情况,从武器到工业制造。 最初是大规模解放和公民赋权的工具,最终被国家与最大和政治联系最密切的公司合作收归国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20 世纪这种暴行的最好例证:军火制造商是那场暴行的唯一真正赢家,而国家获得了从未真正放手的新权力。
很难理解“大战”对整整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震撼。 我的导师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写了一篇非常周到的 反射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技术爱好者的天真自由主义,大约在 1880-1910 年间。 这一代人在各个方面都看到了进步解放:奴隶制的终结、新兴的中产阶级、旧的权力贵族的崩溃以及新技术。 所有这些都促成了钢铁的大规模生产、崛起的城市、无处不在的电力和照明、飞行以及从室内管道和供暖到大规模食品供应的无数消费者改进,从而实现了巨大的人口变化。
阅读那个时期的伟人,他们对未来的乐观是显而易见的。 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马克吐温持有这样的观点。 他对美西战争的道德愤慨、南方家族争斗的残余以及反动的阶级偏见在他的著作中无处不在,他总是带着一种深深的不赞成感,认为这些复仇主义思想和行为的迹象肯定是一代人远离完全到期。 他分享了时代的幼稚。 他根本无法想象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的屠杀,让美西战争看起来像是一场演习。 奥斯卡·王尔德、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威廉·格莱斯顿、奥伯隆·赫伯特、阿克顿勋爵、希莱尔·贝洛克、赫伯特·斯宾塞等人都对未来抱有同样的看法。
罗斯巴德的观点是,他们的过度乐观、他们对自由和民主胜利必然性的直觉以及他们对技术使用的总体幼稚实际上导致了他们认为文明的衰落和衰落。 他们对美好未来的信心——以及他们对国家的恶意和公众的顺从的低估——创造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像其他方式那样被驱使为真理而努力。 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和平与福祉不断进步的观察者。 他们是辉格党人,他们含蓄地接受了黑格尔式的观点,认为他们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例如,对于赫伯特·斯宾塞,罗斯巴德写道 严厉的批评:
斯宾塞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 但是,随着社会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病毒在他的灵魂中蔓延,斯宾塞放弃了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运动,尽管起初并没有在纯粹的理论中放弃它。 简而言之,在期待最终的纯自由理想的同时,斯宾塞开始认为它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是在经过数千年的逐渐演变之后,因此,事实上,斯宾塞放弃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战斗的激进信条; 并在实践中将他的自由主义限制在对 XNUMX 世纪后期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的疲倦、后卫行动上。 有趣的是,斯宾塞疲倦的战略“右转”很快也变成了理论上的右转。 因此,斯宾塞甚至在理论上也放弃了纯粹的自由。
罗斯巴德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如此敏感,是因为他的思想观念形成的奇怪时期。 他经历了自己的挣扎,以适应实时政治的残酷毒害意识形态理想主义的纯洁性。
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时,罗斯巴德范式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 到 1963 年至 1964 年,他发表了他的巨著经济学论文,对大萧条起源的经济学进行了重构,并将成为他遗产的二元论的核心放在一起:历史最好被理解为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斗争. 他最好的政治经济学书籍之一—— 力量与市场 – 几年后出现的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写的,但没有出版,因为出版商觉得它太有争议了。
与国家无情的掠夺相比,这种观点隐含着对自由企业普遍价值的普遍假设。 它在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都具有真理之环:小企业与政治的阴谋和骗局相比,企业家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与官僚军队的谎言和操纵相比,通货膨胀、税收和战争的严酷对比商业生活的和平贸易关系。 基于这种观点,他成为了 20 世纪最重要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倡导者。
罗斯巴德在那些年里也因从未加入右翼而成为冷战的拥护者而著称。 相反,他认为战争是国家主义最糟糕的特征,是任何自由社会都应该避免的。 而他曾经在 国家评论,他后来发现自己是憎恨俄罗斯和喜欢炸弹的保守派教令的受害者,因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流派,接管了自由主义者这个名字,直到最近才被喜欢自由主义者这个名字的人复兴但意识到这个词早已被它的敌人盗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挑战了罗斯巴德二元论。 他并没有忘记,冷战安全国家建设之外的主要推动力是私营企业本身。 自由企业的保守派拥护者完全没有区分独立于国家而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力量和那些不仅靠国家生活而且通过战争进一步将暴政枷锁对民众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征兵制和一般工业垄断。 看到他自己的二进制文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挑战,促使他找到了一个体现在他的日记中的智力项目 左和右,于 1965 年开业,一直运行到 1968 年。在这里,我们发现了 XNUMX 世纪下半叶最具挑战性的一些写作和分析。
第一期的特色可能是他关于政治史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 “左、右和自由的前景。” 这篇文章来自罗斯巴德向左转热的时期,仅仅是因为他只是在政治光谱的这一边发现了对冷战叙事的怀疑,对工业垄断的愤怒,对反动军国主义和征兵的厌恶,顽固的反对对侵犯公民自由的行为。 并普遍反对这个时代的专制主义。 很明显,他当时在左边的新朋友与今天醒来/锁定的左边有很大不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巴德也对他们以及他们对经济无知的坚持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普遍仇恨而不仅仅是裙带派的仇恨。
几十年来,随着罗斯巴德越来越倾向于将阶级理解为政治动态的宝贵需求,大企业利益与国家密切相关,以及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对比是必不可少的启发式地堆积在他的旧状态与市场二元之上。 当他更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时,他开始采用我们现在与民粹主义联系起来的许多政治比喻,但罗斯巴德也从未完全适应过这个职位。 他拒绝粗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比任何人都清楚右翼的危险,并且深知民主的过激行为。
尽管他的理论保持不变,但他从这里到那里的战略前景经历了多次迭代,最后一次是在他 1995 年英年早逝之前,他与最终使特朗普掌权的新兴运动产生了联系,尽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罗斯巴德会像对待尼克松和里根一样对待特朗普。 他认为他们俩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谈论一场精彩的比赛——尽管从未始终如一——并最终在没有原则现实的情况下通过反建制言论背叛了他们的基地。
理解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的一种方法是我开始反思的简单观点。罗斯巴德梦想着一个自由社会,但他从不满足于仅仅理论。像影响他的主要知识分子活动家(弗兰克·乔多罗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安·兰德)一样,他相信在他所处的时代,在他所获得的知识和政治领域做出改变。这促使他对企业权力和一般权力精英的特权更加怀疑。到他去世时,他已经远离了年轻时的简单二元论,面对 1960 世纪 1990 年代到 XNUMX 年代的严峻现实,他必须这样做才能理解它们。
他会不会像我对大型科技公司的背叛一样感到震惊? 不知怎的,我对此表示怀疑。 他对同时代的工业巨头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并全力以赴与他们作战,这种热情导致他改变联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推动他的主要事业,即把人类从我们周围的压迫和暴力力量。 罗斯巴德是国家的敌人。 许多人甚至注意到电影中吉恩哈克曼的角色的相似之处。
我们这个时代惊人的政策趋势确实在呼吁我们所有人重新思考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尽可能简单和稳定。 出于这个原因,布朗斯通出版了各方面的思想家。 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不满。 我们现在知道,没有什么是一样的。
我们放弃了吗? 绝不。 在封锁和医疗任务期间,国家及其企业盟友的权力真正达到了巅峰,让我们惨遭失败。 我们的时代呼唤正义,呼唤清晰,呼唤改变以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明。 我们应该睁大眼睛和耳朵来处理这个伟大的项目,以听取关于我们如何从这里到那里的不同观点。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