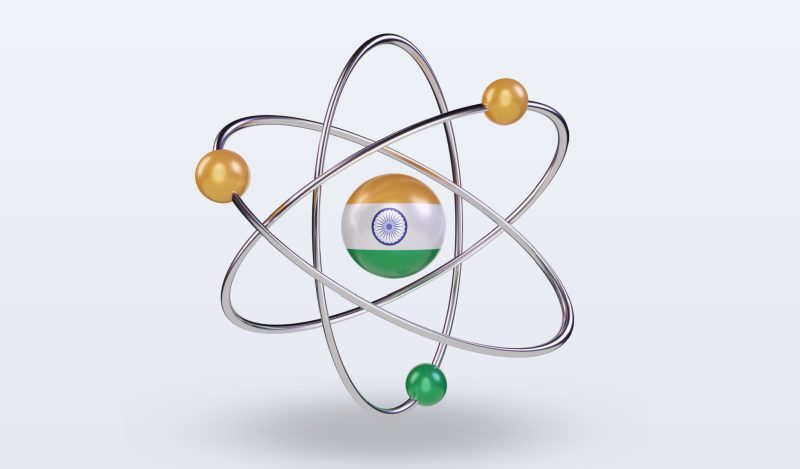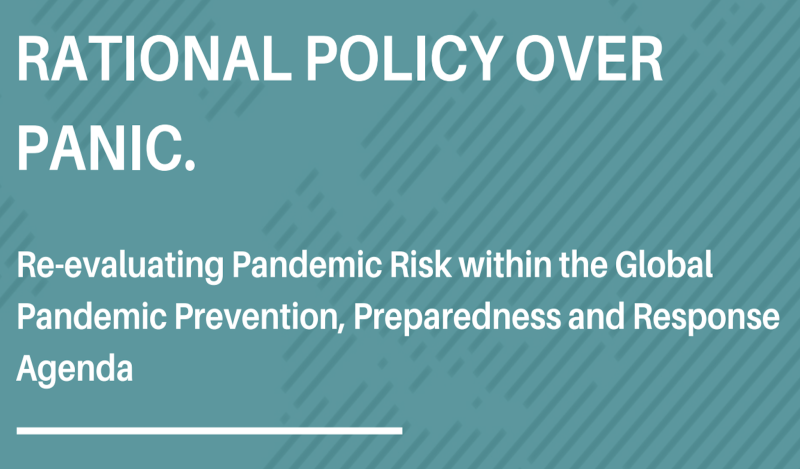我非常感谢你关于 生病和孤独. 这是我的故事。
我是一个健康的 52 岁女性,唯一的既往疾病是高血压。 我在 2021 年 XNUMX 月下旬生病了。最后我因缺氧和晕厥不得不去医院急诊室。
我丈夫不得不把我送到急诊室,他甚至不被允许带我进去。在我计划的疯狂之前,我的直系亲属或大家庭中没有人独自一人在医院里。
我记得小时候在候诊室露营,睡在拉好的椅子上。 如果生病的亲人需要任何东西,随时准备好。 护士总是过度劳累,像补充冰水或在我们的人无法处理信息时提出正确的问题等平凡的事情已经成为我们的标准做法。
我一直认为,拒绝让住院患者成为辩护人是残忍和不安全的。 我从来没有让我的一个孩子独自一人(我曾多次睡在不舒服的医院躺椅上)。 我每分钟都和我丈夫待在一起,我的父母一直有我们中的一个人昼夜不停。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家几乎每个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被拒绝接受早期治疗,然后被单独监禁在医院里。 死亡崇拜协议几乎要了我的命。
21 天里没有人可以见我。 我被剥夺了人际交往。 博士。 会站在门口给我打电话商量治疗。 他们弄丢了我的眼镜。 我变得迷失方向和害怕。 我是一个稳定的人,对医疗流程和术语有比较牢靠的把握。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为患有一种罕见的使人衰弱的疾病的女儿寻找合适的治疗方法。 我也在医学领域工作,所以我很乐意讨论测试结果和药物。
我没有为孤独的绝对恐怖做好准备,不再相信医生真的希望我活下去。 随着我变得越来越昏昏欲睡和迷失方向,我一直试图成为自己的拥护者,并乞求有权尝试我研究过并知道会帮助我的药物和维生素。
如果我能够站起来,我会走出去,但旨在杀戮的协议行动很快。 我在那所监狱里呆了 5.5 周。 当他们确实允许访客时,它是每天一个,访问时间在下午 5 点结束。 我丈夫直到 4 点 45 分才下班。 如果有人来了,只能停留几分钟,那就是你的一个访客,其他人都不准。
最初的几天后,我并没有太多清晰的记忆,但幻觉、噩梦和渴望与人接触的绝望总是会历历在目。 我相信如果我与战俘交谈,我们的情感创伤可能是相似的。 对于可怕的反人类罪行,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天堂,都会有一个清算的日子,“我只是听从命令”的说法不会免除! ~ 安吉拉·迪特曼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