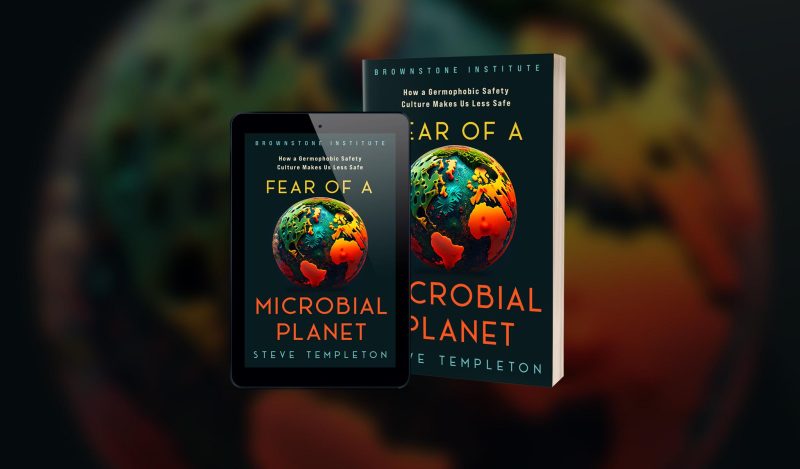作为我书籍研究的一部分,我与众多关于 COVID 科学和医学的专家进行了交谈。 我已经转录了其中两个讨论 发布 点击此处. 最近,我与丹麦裔美国医生和流行病学家 Tracy Beth Hoeg 讨论了北欧国家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如何解释 COVID 反应的差异。 为清晰和相关而编辑的成绩单。
ST:首先,你有一个有趣的背景。 我想听听你谈谈你是如何进入医学和流行病学的,以及你是如何来到丹麦的。
TH:我来自威斯康星州,去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大二的时候我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我基本上有过改变生活的经历,因为我曾涉足音乐和写作、艺术和文学。 然后我遇到了一位德国医生,我和他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说:“如果你想终生环游世界,你应该成为一名医生。 作为一名医生,你可以在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获得有用的技能。” 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学生,你并没有真正的实际技能。 在巴黎大学完成了电影和哲学的学习后,我回到了麦迪逊并参加了预科课程,并且很喜欢它。
这么晚考MCAT的时候,又要休学一年,所以又搬回法国,在一所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 我教中学英语。 另一个惊人的体验。 之后我去了威斯康星医学院的医学院并参加了眼科住院医师计划,然后遇到了我的丹麦丈夫。 在我开始居住前几天,我最终发现自己怀孕了。 然后我发现了十五天的产假和我必须支付的医疗费用。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做出了搬到丹麦的疯狂决定。 我在紧急护理部门工作了一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申请去丹麦。 我学了丹麦语,因为你必须懂丹麦语才能在那里当医生。
在斯堪的纳维亚行医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我必须参加医学院的课程或一定数量的考试,有些考试你必须考一百个,否则他们不允许你获得医疗执照。 我花了大约六周的时间,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开始了医生的工作。 起初,我是内科,然后是眼科。 然后部门注意到我在哈佛医学院期间做过关于衰老和痴呆的研究,他们问我是否会考虑指导一项大规模的人口健康研究。 我们有超过 XNUMX 名参与者参与了这项研究,我聘请了 XNUMX 名护士与我一起工作,我们对所有这些人和视网膜眼底照片进行了全面的眼科检查,并进行了将我们发现的结果与整体健康相关联的研究。 这导致了许多其他不同的研究,我最终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了流行病学博士学位。 我在丹麦待了七年,生了第二个孩子,享受了很棒的产假。
我也是一名半职业跑步者,我对运动医学产生了兴趣。 我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研究人员一起做了一项关于长跑运动员视力丧失的研究,他让我对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感兴趣,并做物理医学和康复,这是我现在的专业。 那是大流行前六个月。
ST:当你七年后回到美国时,你有没有感觉到文化冲击,离开那么久?
TH: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不记得英语了! 我不记得如何写医疗记录和基本的医疗材料,显然它回来了,但再次阅读笔记以及人们如何写它们是一种文化冲击。 与七年前的记忆相比,一切似乎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 直到我们搬到美国,我的孩子们才知道我会说英语。
这是一种不同的医学文化。 我对 VIP 患者的想法以及患者护理如何由他们拥有的金额决定感到震惊。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惊。
ST:然后 COVID 来袭,你注意到了其他一些文化差异。
TH:我认为世界上很多人一开始的反应都非常相似。 人们在看意大利和中国,在冬天的早些时候,我想“这看起来不太好!” 我一直在关注这些数字,CDC 的反应速度让我吃惊,尤其是检测问题,我注意到欧洲的反应速度要快得多。 我一直对美国在人口健康方面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但我真的没有预见到——我不想用无能这个词——更令人失望的是(疾控中心)对大流行。
但对我来说真正突出的第一件事,我知道你想谈论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开办学校的速度有多快。 在丹麦,他们封锁了,在瑞典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关闭小学,只关闭了中学。 一开始,我认为丹麦的做法是对的,但当时还不清楚谁是对的。 我认为丹麦所做的事情是如此正确——他们并没有长时间封锁,因为他们害怕长期封锁的后果,而且他们知道最小的孩子会受到最大的影响。 他们知道孩子们没有受到 COVID 的严重影响,他们知道除非孩子们有地方可去,否则你无法开放整个国家。 所以他们开辟了蒂沃利花园作为孩子们的户外空间,并使用了女童子军和男童子军的俱乐部会所。 这只是动员整个国家努力让这些孩子重返学校,以便其他人可以重返工作岗位,人们可以继续他们的生活。
不仅仅是丹麦。 那年春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开学了,我们看到在欧洲各地的学校开学后病例有所下降。
ST:回到测试,我在丹麦有一个合作者,他基本上将他的整个实验室重新用于测试。 他在做基础科学,没有直接临床。 就这么快,他就能够扭转他的实验室并进行几个月的测试。 这不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做的任何事情。
TH:在真正体验美国方式之前,我体验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方式。 它非常有活力,有很多机会申请助学金,而且不难弄清楚如何去做。 你只受到你的创造力的限制。 当我回到美国时,我看到了 NIH 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来填写申请并找到一个特定的人与之合作,而你必须进行他们的研究。 这是非常不灵活的。 我有很多我感兴趣的研究项目是在超级马拉松运动员身上做的,现在看着 COVID 听起来并不重要,但我怎么会在这里做呢? 而在丹麦,我认为找到一些小组织来资助这样的事情会很容易。
ST:我想回到北欧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人们喜欢指出结果的差异,尤其是在大流行的头几个月,以及瑞典的表现不如其他国家。 人们喜欢大肆宣扬这一点,仿佛这是对丹麦和挪威采取的更严格措施的认可。 但是,对我来说,这三个人都非常轻,相对于欧洲、美国和美洲的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 除了很早就发生的封锁之外,这三个国家之间的真正区别是什么?
TH:丹麦实际上再次进行了几次封锁,而不是完全封锁,但他们再次关闭了学校。 但他们很矮,而且他们总是有地方让基本工人的孩子去。 这非常重要,因为 90% 的妈妈(如果不是更多的话)都是全职工作,这比美国要高得多。 因此,即使他们关闭了学校,这也是暂时的。 但瑞典根本没有关闭学校。 所以这就是区别,据我所知,挪威的做法与丹麦的做法非常相似,如果有已知的变体,就会间歇性封锁,但他们似乎一直在从英国得到预测。 甚至我的丹麦医生朋友都说,“我们为什么又要封锁了? 他们对学校再次关闭感到非常沮丧。
但最后,我认为瑞典的总体超额死亡率略高于丹麦和挪威,但相差不大。 是马丁(库尔多夫)提出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好观点,瑞典刚刚度过了寒假,很多案件都进入了斯德哥尔摩。 我不确定你是否谈到过这个……
ST:哦,在我书的最后一章。
TH:好的好的,你已经完成了。 你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说我认为丹麦是对的,但现在很难说,因为他们的结果总体上是如此相似。
ST:实际上,如果你这样做了 年龄调整的超额死亡,没有一个北欧国家有任何超额死亡。
TH:哦,年龄调整? 有趣的。
ST:一切都变得消极。
TH:哦! 事实上,我确实看到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会再看一遍。 谢谢你提到这一点。
TH:还有丹麦,他们宰杀了水貂……
ST:对! 我确定这是关键,实际上……
TH:这显然行不通。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僵尸貂,但是有一群没有死,他们只是从地里回来了。
ST:哇。
TH:我知道。 但是他们已经为杀死水貂而道歉,这是丹麦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道歉。 我喜欢它,即使它有点苦涩,因为就像很多事情一样,他们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们还为儿童接种疫苗表示歉意,说:“你知道,我们错了。” 嗯,他们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信任度如此之高的部分原因,这就像公共卫生和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
ST:在 刊文 你写的 明智的医学,您写到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人们似乎对公立学校教育和儿童发展负有特殊责任,而我们似乎没有,出于某种原因在过去两年中暴露出来。 你如何解释这种文化差异?
TH: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学校里的孩子,他们优先考虑让父母和家庭有时间陪伴孩子成长,它建立了这种文化,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照顾孩子并注意到他们的重要性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个突出特点,在美国不存在。 我认为这与工作周的结构有关,即更短、更多的休假时间以及围绕病假和休假之类的灵活性。 如果他们需要与家人一起做某事,没有人会认为其他人是软弱的。 人们喜欢吹嘘他们在周末与家人一起进行的冒险以及他们为孩子所做的事情。 一个美好的生活就是你如何对待你的孩子。 这里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场比赛——我的孩子们在这个或那个竞争的事情上。
ST:这实际上是对我真正喜欢谈论的内容的一个很好的延续,因为我喜欢将美国的反应归结为我们在美国这里拥有的这种安全文化所促成的。 刚刚失控了。 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工作场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它希望他们死去。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比如几十年。 现在,这些直升飞机父母养大了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的人,(他们要求)将风险从他们的生活中完全消除。 我有这种感觉,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地的文化差异实际上是他们如何看待应对大流行病责任的关键。
ST:几年前我在丹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演讲,因为我在那里有合作者,他们邀请了我。 当我与他们共进晚餐时,我的主人谈到了丹麦和美国之间的安全文化差异。 他们提到了一个故事,关于几年前一对丹麦夫妇去纽约市的一家餐馆,把他们的孩子放在人行道上的婴儿车里,这样他就可以看到人们走过。 他们被捕了,丹麦人对此感到震惊。
TH:我也是! 那是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或者我想在那之前不久。 我记得我在想,把你的孩子留在这样的咖啡馆外面有什么问题? 嗯,我有丹麦人的回应,因为当你把他们像小婴儿一样带到日托时,他们都睡在外面的小床上。 孩子们骑自行车步行上学。 这里的父母不要让孩子自己出去玩,要独立。 它还与城镇和住房结构的设置方式有关,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步行和骑自行车。
当我听说人们担心孩子们在户外上学时,我想为什么这令人担忧? 在丹麦,孩子们在户外淋雨,在寒冷中。 您只需让他们穿上防水服装即可。
这里有很多层额外的保护让我很恼火,甚至到了你无法打开窗户的建筑物的地步。 即使在那里的医院里,也像是,“哦,只要打开窗户或到甲板上出去。” 也许这与一个更爱打官司的社会有关,但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更加自然,他们在户外度过了很多学生时光。 这就像 Rudolph Steiner 的教育方法,我不知道你对它有多熟悉,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玩耍和与人建立联系以及在外面,而不是“你必须学会阅读和写作”特定的时间。” 所以这种方式有点不同。
ST:这里是——“如果你保护他们的安全,你就是在照顾他们。” 这与促进他们的发展不同,这在丹麦听起来更像。 不让孩子从单杠上掉下来学习自己的极限。 这是他们发展的一部分。 在我孩子上的学校,我女儿从单杠上摔下来伤了她的胳膊,我们不得不给它拍了 X 光片,另一个孩子实际上在同一周摔断了他们的胳膊,他们把它包起来(单杠)小心胶带,几个月没有使用它,直到最后孩子们把它撕掉并重新开始使用它。
TH:对他们有好处!
ST:是我非常喜欢的校长,他说“这可能不适合他们玩。” 我说,“嗯,原因是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了。” 现在,当他们真正玩单杠之类的东西时,他们还没有更早地了解自己的极限,所以当他们接触到这些东西时,他们更容易受伤。
TH:当然。
ST:然后回应是“我们需要让这更安全”,而不是“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教他们了解自己的极限。” 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在用传染病做这件事。 因为你在 RSV 中出现了很大的峰值,以及诸如让孩子们远离彼此的事情。 流感也。 后来他们感染了一些这些感染,有时情况会更糟,这取决于它是什么,显然。 现在,人们在谈论工程建筑,所以它是完全无菌的空气。 我觉得我们正朝着多个方向走这条路。
TH:生活并非没有风险,我认为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比这里更受认可。
ST:年轻人的疫苗接种也是如此。
TH:因此,就安全主义而言,这场流行病的关键在于最终对那里的孩子们(在丹麦)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他们让他们更快地恢复正常,然后他们更快地意识到这没关系。 我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过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关闭诊所几个星期,然后我害怕回去,一旦我在那里,就像,“哦,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认为那是美国的学校发生了什么。 一旦人们有大量的时间在他们的脑海中建立起关于学校重新开放时会发生什么的事情,那么就没有时间去发展那种极端的恐惧了,尤其是在瑞典。 我确实认为它的很大一部分,在精神上,只是没有等待那么久,而是让它像那样建立起来。
ST:这就是整个心理学。 有了这些命令,每个人都被迫表现出互相害怕的样子,而你没有坚持表明,“看,我在这里过着正常的生活,面对每个人的说法,我还活着,而且那么,也许我得到了轻微的感染或其他什么。” 在有更严格限制的地方,这实际上是一个慢得多的过程。 但有趣的是,人们不相信其他地方是正常的。 我和爱荷华州的一个有孙子孙女从纽约来访的人交谈过,他说他们花了五天时间才在外面不戴口罩。 爱荷华州没有人在里面做……
TH:是的,完全是你亲眼所见。 这正是我的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他们实际上在 2020 年有暑期学校,之后的老师们决定,“我想还可以。” 这很奇怪——我们有一所类似于公立学校的多元化私立学校,不是很花哨,但信息并没有从一所学校或教区传播到另一所学校或教区。 这很奇怪。
ST:当你试图告诉他们一个地方完全正常时,人们不相信,他们仍然被封锁。 他们只是拒绝相信。
TH:即使在我们的威斯康星州伍德县之后 根据一项研究,,这里总是有别的东西,“嗯,那是因为它位于威斯康星州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白人。” 我当时想,“哦,天哪,总会有事的。” 然后他们说,“他们可以打开窗户在外面吃饭,我们就像,“嗯,实际上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六英尺的距离,无法打开窗户。” 那是十月下旬和十一月,天气寒冷。 人们仍然喜欢,“我们就是无法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复制它。” 你知道,它总是一些东西,移动的球门柱。
ST:您从谈论在 COVID 期间学校如何安全并进行后续研究,到谈论针对年轻人的疫苗以及围绕该问题的安全问题以及成本/收益权衡。 显然,当您深入研究这些主题时,它们并不总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给我一些关于这些话题是如何被政治化的想法,以及你是如何对它们产生很多批评的。
TH:首先,对于儿童疫苗,我很惊讶它们的批准速度如此之快,然后很高兴高风险的孩子有可用的疫苗。 然后,它来自,“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对抗严重疾病的功效。 我们不知道“长期防止传播”成为这种文化事物的效果,在这种文化中,你有所有同龄人的压力让你的孩子接种疫苗,即使他们是健康的,或者是学校和体育部门规定的。 所以我的兴趣一直是“我们能否对儿童进行某种风险/收益计算,尤其是这种疾病风险如此低的健康儿童?” 这真的让我很困扰,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在我们有心肌炎的信号之后,我自己也有一个青春期的儿子。
我们从以色列获得了这些信息,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西雅图的一名急诊医生,她看到了所有这些十几岁男孩和年轻男性的心肌炎病例。 这个词没有传出去。 除了来自以色列的报道外,我觉得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 这就是导致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数据库研究. 我天真地认为人们会想知道这种情况在那个年龄组和男性与女性中的普遍程度。 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在我们没有太多信息并且被世界上一些顶级期刊考虑的时候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但我现在知道有争议的话题很难发表; 当然,它最终出版了。
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向同一人群推荐加强剂,而且您知道我们的风险/收益分析甚至没有发现第二剂对青春期男孩是值得的,甚至可能对已经接种过的孩子进行第一剂其他方面健康的感染者。 时至今日,CDC 似乎完全无法进行风险/收益分析,而且确实很麻烦。 我想为这个主题做出贡献,然后说,好的,现在我们有了这些信息,现在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政策。 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只是不断地推荐更多。
ST:所以,你在丹麦有你的同龄人,你仍然和他们谈论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们对这里正在发生或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TH:我的公婆很难相信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但同时我们的孩子也在上学,所以这很正常。 与我交谈过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丹麦人,他们最难相信的是我们让年幼的孩子戴口罩。 我记得和一位瑞典眼科医生朋友交谈过,他非常喜欢,“我们需要封锁,我们需要让每个人都戴口罩。” 我们对此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但我们都非常重视 COVID。 然后他说了一些关于他诊所里有人戴口罩的评论,我说:“是的,让孩子戴口罩真的很难,”他说,“不,我不是在说孩子。 孩子们为什么要戴口罩?” 尽管他非常担心 COVID,但在孩子脸上戴口罩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
我认为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孩子失学无处可去。 这对我来说是最难理解的,这些孩子不仅不能上学,而且没有安全的地方去。
ST:有一次我和学区主管谈过他们会如何推迟上学,即使天气很冷,或者因为一英寸的雪而取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正在提高安全性。 但我的论点是,有很多孩子的学校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在他们通常在学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学校有责任吗? 如果孩子们在寒冷中等公共汽车并且拒绝穿外套,那不知何故是学校的问题,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想问的最后一件事——你知道你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医生)朋友,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并在加利福尼亚谈论有关口罩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 旨在惩罚传播错误信息的医生的立法. 显然,以你的名声——
TH:——是的,我无可挑剔的名声。
ST:——这对你来说可能是个问题。 这一切的状态如何?
TH:我很担心。 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并且非常致力于向我的患者提供我所知道的信息。 我认为这是我的病人真正看重我的东西。 实际上,我有很多患者来找我询问有关 COVID 的问题,甚至直到今天,关于助推器、口罩、疫苗的有效性等问题。 你知道,我是一名 PM&R 医生,但我们会看到各个年龄段的患者,他们的身体状况各不相同。 知道法案或法律的存在使我以一种我什至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偏执。 我认为其他医生也有这种感觉,那些一直致力于跟踪最新研究的人现在想知道,“加州医学委员会有多赶上?” 有人写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我们会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应用程序,告诉我们每天的共识是什么吗?” 这就是它所需要的,因为事情变化如此之快,我们的知识也在不断发展。
我仍然收到在线威胁,人们举报我,人们告诉我我会有假病人来举报我。 那只是没有帮助。 它并不能改善病人的护理,不得不担心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是否是别人认为的共识,无论是对还是错。 我们真的应该专注于尽我们所能说出真相。
ST:会不会像 Twitter 或 Facebook 监狱一样,人们因引用已发表的研究或辉瑞的新闻稿而受到审查?
TH:被提上议案的参议员之一,潘参议员,他一直主张在没有有效性证据的情况下给儿童戴口罩,并在没有进行真正彻底的风险/收益分析的情况下强制接种疫苗。 就像 Jay Bhattacharya 所说的那样,说“我是无所不知的人”是极端的狂妄自大。 不,我们应该一直共同努力寻找答案。
转载自作者 亚组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