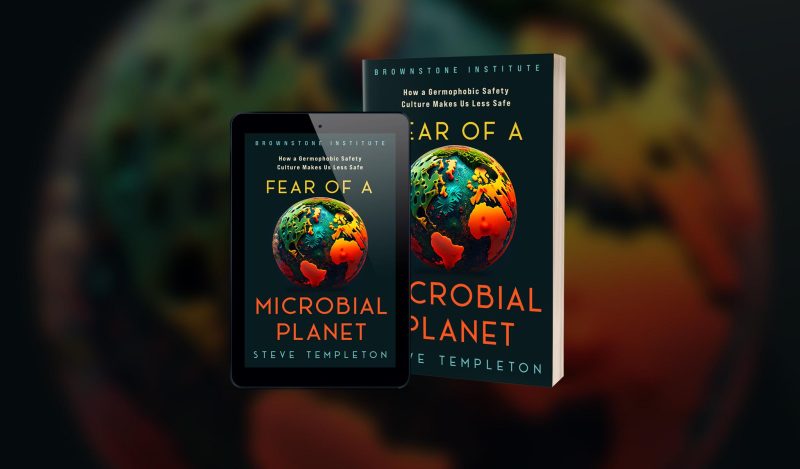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将真相隐藏在健康美德外表背后的艺术。 据推测,它与人类一样古老。 墨索里尼只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将他的专制思想隐藏在沼泽排水、村庄更新、孩子上学和准时运行的火车背后。 1930 年代纳粹主义的画面不是破碎的窗户和在街上被殴打的老人,而是快乐微笑的年轻人在户外一起工作以重建国家。
把这样的标签放在现在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们承载了很多包袱,但这也有助于确定我们认为当前的包袱是进步的,实际上是倒退的。 1930年代那些快乐微笑的年轻人实际上正在接受自以为是、诋毁错误想法和集体服从的艺术训练。 他们知道他们是对的,而另一方就是问题所在。 是不是很熟悉?
过去两年的社会变化是由“公共卫生”定义和主导的。 因此,寻找过去的公共卫生类比以帮助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驱动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正确的。 我们目睹了我们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和代表他们的协会呼吁对医疗选择进行积极的歧视和强制。 他们提倡使他人贫困的政策,同时维持自己的工资,控制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规定他们如何哀悼死者。
医院拒绝为那些做出医院不喜欢的无关医疗选择的人进行移植。 我目睹他们拒绝让家人接触垂死的亲人,直到他们接受他们不想要的注射,然后允许立即接触,从而确认所寻求的不是免疫力,而是顺从。
我们都看到著名的卫生专业人员公开诋毁和诋毁那些试图重申我们都接受过培训的原则的同事:没有胁迫、知情同意和不歧视。 一位专业同事没有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是在一次关于证据和伦理的讨论中告诉我,公共卫生医生的作用是执行政府的指示。 集体服从。
“更大的好处”证明了这一点是合理的——这是一个未定义的术语,因为在两年内没有任何政府推动这种说法,发布明确的成本效益数据,证明“好处”大于危害。 然而,实际的计数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重点。 “更大的利益”已成为公共卫生专业废除个人权利至上概念的理由。
他们已经决定,为了“保护”大多数人,歧视、污名和压制少数群体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那些宣传诸如“未接种疫苗者大流行”或“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等口号的人知道将少数族裔作为替罪羊的意图和潜在结果。
他们还从历史中知道,这些陈述的谬误性质并不会妨碍它们的影响。 法西斯主义是真理的敌人,而不是它的仆人。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建议我们称铁锹为“铁锹”。 我们如实陈述事情,我们说的是实话。 疫苗是一种具有不同益处和风险的药品,就像树木是长着叶子的木头一样。 在任何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平等和内在价值的社会中,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利,而不是医生或政府。
基于医疗保健选择的污名化、歧视和排斥,无论是针对 HIV、癌症还是 COVID-19,都是错误的。 由于对使用安全药物的不同看法而排斥和诋毁同事是傲慢的。 谴责那些拒绝遵守违背伦理道德的命令的人是危险的。
仅仅为了遵守“团体”而盲目地听从政府和企业的指令与道德公共卫生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都与上个世纪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我参加的公共卫生讲座中所教授的内容。 如果这就是我们现在希望发展的社会,我们应该站出来说明这一点,而不是躲在诸如“疫苗公平”或“共同参与”等虚假美德的表面后面。
让我们不要被“左”和“右”的政治细节所束缚。 1930 年代欧洲两大法西斯政权的领导人都是从“左翼”中崛起的。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更大的利益”的公共卫生概念来淘汰低劣的思想家和不服从者。
我们目前的状况需要自省,而不是党派之争。 作为一个职业,我们遵守了歧视、污名化和排斥的指令,同时模糊了知情同意的要求。 我们帮助消除了基本人权——身体自主权、教育、工作、家庭生活、行动和旅行。 我们追随企业独裁者,无视他们的利益冲突,并在我们的公众变得更穷的情况下丰富他们。 公共卫生未能让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少数有钱有势的少数人的喉舌。
我们可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它可能会以上次的方式结束,除非可能没有其他人的军队来推翻我们支持的怪物。
或者我们可以找到谦逊,记住公共卫生应该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那些试图控制他们的人的工具,并将怪物从我们中间赶走。 如果我们不支持法西斯主义,我们就不能成为它的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遵循我们的职业所依据的基本道德和原则来实现这一目标。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