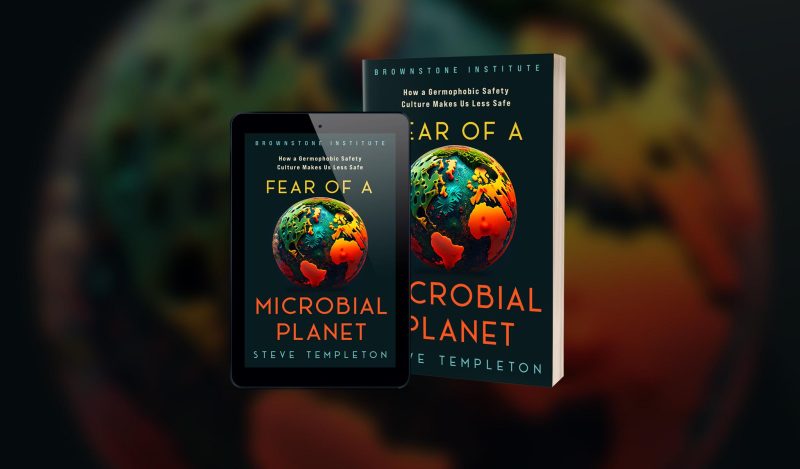我一直在仔细研究大流行开始时发生的事情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它再次发生。
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回答。 一个问题是病毒本身的起源——它是人工设计的还是自然的,它是什么时候出现或泄漏的,在哪里,以及是什么解释了它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行为? 第二个问题涉及我们回应的起源:封锁、社会疏离、口罩和其他非药物干预措施 (NPI) 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每个人都采用它们,即使它们以前从未使用过,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代价高昂的措施会取得什么意义?
这就是我目前认为发生的事情——这篇文章是故意简洁的,作为一个总结。 按照链接阅读有关每个方面的更多详细信息。
锁定和 NPI 议程始于 布什白宫 2005 年——尽管中国以前曾使用过封锁/NPI 为应对2003年的非典 并声称取得了成功(尽管 SARS 无处不在,而不仅仅是在使用 NPI 的地方)。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是 担心生物攻击 在 9/11 和伊拉克入侵之后 问他的团队 拿出全社会的反应。
MTT综合医学训练疗法国际教学中心 禽流感恐慌 为新出现的“大流行准备”议程增添了动力(尽管恐慌最终化为乌有)。 该团队提出的计划是基于使用 NPI 来保持社交距离——这与中国使用的非常相似,尽管团队成员自己并没有将他们的想法归功于中国,但奇怪的是,一名成员的高中科学项目 14岁的女儿.
这种严厉的生物安全战略就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 它包括强调疫苗的快速开发和数字疫苗通行证的部署作为限制的退出策略,特别是 mRNA 疫苗,它被视为一种可打印的疫苗,可以快速适应新出现的病原体。
对 mRNA 疫苗的战略偏好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卫生当局似乎在寻找腺病毒载体疫苗(强生、阿斯利康)的安全问题上比 mRNA 疫苗(辉瑞和 Moderna)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比尔·盖茨是生物安全运动的早期皈依者,并成为主要赞助人,尤其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对生物安全运动的热情降温时。
新的以生物安全为导向、基于 NPI 的大流行防范理念逐渐融入国际政策和实践,包括通过国家大流行计划、 世卫组织指导,以及大流行模拟练习,例如 Event 201,由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014 年,根据非洲生物安全人群的建议,首次实施封锁 为应对埃博拉,并有趣地包括在 2020 年初出现的数百个社交媒体机器人推广该想法的奇怪现象。 谁在 2014 年和 2020 年支持这些“锁定机器人”尚未得到解决。
修补病毒以帮助开发针对潜在大流行病原体的疫苗和治疗方法是生物安全议程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病毒会从实验室泄漏,这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即研究的回报是否值得冒致命泄漏的风险。
在病毒于 2019 年 23 月进入公众意识后,中国将新的生物安全理念付诸行动——尽管有趣的是,直到 XNUMX 月 XNUMX 日,这表明它最初并不认为该病毒是一种威胁; 事实上,起初中国政府因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威胁而受到广泛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乔治高是 CEPI,盖茨资助的生物安全议程机构之一,其使命是“在 100 天内制造大流行性疫苗”。
作为 2003 年和 2020 年 NPI 战略的先驱,中国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成为 NPI 的重要推动者,国家的自豪感和习近平主席的声誉都与他们的成功息息相关。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尽管不一致)加入了这一行列,其 COVID-19 联合任务负责人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 声明 24 年 2020 月 XNUMX 日:“中国已经证明,你必须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你可以挽救生命。”
NPI 最早是由意大利在西方实施的。 2020 年 XNUMX 月上旬,意大利委托 危言耸听的建模研究 来自盖茨支持的生物安全研究所, 凯斯勒基金会,它建议 NPI 控制传播。 当伦巴第的紧急服务机构负责人阿尔贝托·佐利(Alberto Zoli)表示, 不堪重负 XNUMX月中旬,卫生部长 罗伯托·斯佩兰萨(Roberto Speranza) (一位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看到或开始看到封锁是左派的新曙光)实施了西方的第一次封锁,首先是在 21 月 XNUMX 日在伦巴第大区,两周后,当它们看起来奏效时(随着死亡人数的攀升) ), 全国各地。
其他国家随后效仿意大利,而各种生物安全类型,包括像尼尔弗格森这样的建模者,公开和闭门推动议程。 唐宁街 10 号当时的参谋长多米尼克·卡明斯 告诉国会议员 2020 年 XNUMX 月中旬,他受到“比尔·盖茨式的人脉网络”的大力游说,告诉他“彻底重新思考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整个范式”。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在 2020 年初日益严重的恐慌中,世界终于接受了生物安全狂热分子关于 NPI 以“控制传播”以及随后的快速疫苗和数字疫苗通行证的观点. 任何坚持 怀疑或怀疑 随着一种新的流行正统观念在精英中流行,此时公共卫生官员和其他人被解除武装或被封口。
领导人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致力于专制的新议程,而群体思维和恐慌的普通民众的压力也加强了这一议程。 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实时发生的,因为英国政府官员在 2020年XNUMX月中旬 很快 弃 面对危言耸听的造型、敌对的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反对。 幕后的恐慌,尤其是在美国,可能部分是由于一些官员意识到该病毒是(或看起来非常像) 设计.
某些群体的既得利益,如制药公司和工会,在加强危言耸听的生物安全叙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什么促使生物安全人群(其中包括 Richard Hatchett、Robert Glass、Carter Mecher、Rajeev Venkayya、Neil Ferguson、Stefano Merler 和 George Gao 等人物)推动了这一发展? 我相信,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将人类从致命的疾病中拯救出来,并为未来的流行病和生物攻击做好准备。
例如,这显然是推动比尔盖茨的原因。 虽然动机可能参差不齐,但我认为,我们永远不应低估那些真诚地相信他们正在拯救世界的人可能造成的伤害——他们的激进解决方案,无论多么痛苦,对于避免灾难都是必要的。
病毒本身呢? 它出现在不迟于 2019 年秋季——最早的可靠检测证据发现来自以下国家的样本(抗体和抗原) 法国 和 巴西 追溯到2019年XNUMX月。有一些样品测试 较早为阳性,但是这些 缺乏控制 因此更有可能发生交叉反应或被污染。 虽然有些人认为东亚早期波的低传播是早期传播增强了一些免疫力的证据,但在大流行早期这些人群中的低抗体水平不符合这一想法。
SARS-CoV-2 似乎是一种工程病毒,可能是从处理它的样本的实验室意外泄漏的。 该工程的建议是,除其他外,存在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这使得它对冠状病毒具有不同寻常的传染性,并且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它与 SARS 不同,它既是空气传播的,又导致了多年的大流行。 在这种类型的冠状病毒中,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在自然界中是未知的,但通常在实验室中插入以增加传染性。
尽管进行了彻底的搜索和分子钟证据,但在动物身上没有发现病毒的宿主 提示 SARS-CoV-15 需要 43 到 2 年才能从其最接近的已知亲属 RaTG13 自然进化。 广泛的 掩饰 那些负责产生这种病毒的研究的人也证明了它是经过工程改造的。
Omicron也可能 泄露 来自实验室的证据包括它是从一种灭绝的菌株进化而来的,并且它包含所有先前发表的免疫逃避突变。 它可能是为了疫苗研究而创建的。
病毒传播动态的某些方面仍然无法解释。 例如,有几个传播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显不同的动态。
- 出现(2019 年夏秋)- 2019 年 XNUMX 月:全球未被发现的传播,疾病和死亡率负担低。
- 2019 年 2020 月至 XNUMX 年 XNUMX 月:武汉爆发了相对致命的疫情,但在日本、韩国、泰国、欧洲、美国和中国其他地区等其他地方却鲜为人知(无论是否实施了 NPI)。
- 2020 年 2020 月至 XNUMX 年 XNUMX 月:在某些地区和城市(例如伦敦、纽约、巴黎、斯德哥尔摩等)发生一些致命的疫情,主要在西欧和美国,从伦巴第大区(以及伊朗)开始。
- 2020 年夏季:之前未受到严重影响的其他地区(包括美国部分地区)发生了一些致命的海浪
- 2020-2021 秋冬:全球大部分地区爆发致命疫情,但印度或非洲除外。
此后,Alpha、Delta和Omicron变种相继出现,每一个都引起了新的全球浪潮,包括在印度(与Delta),最终在东南亚(与Omicron)。
我的怀疑是,这些变化的动态主要来自病毒本身(变体)的变化以及它们如何与人类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尽管不可否认 早期阶段的证据 稀疏。
分子钟证据 提示 2019 年 2020 月至 2019 年 XNUMX 月首波疫情背后的变异共同祖先在 XNUMX 年夏季至秋季首次感染人类。为什么它在武汉才开始致命 2019年十二月,然后直到 2020 年 2020 月的伦巴第和伊朗,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完全清楚。 一些地方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致命的爆发,例如 2020 年夏季、21-2021 年冬季、2021 年春季(印度),甚至在东南亚,22-XNUMX 年冬季。
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这不是因为潜在的病毒不是造成大多数死亡的原因,而是正如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它是恐慌/NPI/治疗方案。 这是因为我在数据中没有看到死亡浪潮发生的时间与恐慌程度、NPI 严格性或治疗方案之间有任何明确的关系(例如,瑞典、南达科他州和白俄罗斯等没有恐慌的地方仍然看到大量死亡浪潮2020 年死亡人数)。 主要因素似乎是所涉及的变体。 布金和同事 注意 SARS-CoV-2 基因组中的单个氨基酸取代“可能会增加对人类的致病性和传染性”。
一些谜团仍然存在,尤其是关于中国知道什么以及何时知道的。 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意识到病毒正在传播,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是泄密? 武汉病毒所冠状病毒数据库于12年2019月XNUMX日下线 信号 是它当时已经知道或怀疑某些事情,还是只是围绕冠状病毒研究的一般机密的一部分?
美军是否知道湖北省(武汉为首府)爆发病毒疫情? 2019年 十一月? 这是新冠病毒还是季节性流感? 为什么在 31 月 23 日宣布病毒后,中国直到 XNUMX 月 XNUMX 日才封锁武汉——这与政府支持的 报告 24 月 XNUMX 日得出结论,人类传播正在发生(尽管它的效率模棱两可)?
同一份报告还提供了有关 41 月武汉首批 49 名 Covid 住院患者的详细信息,称他们的中位年龄为 15 岁,三分之二以上没有潜在疾病,六人(XNUMX%)死亡。 与其他地方的 Covid 患者相比,为什么这些患者如此年轻和健康,而在整个秋冬季,这种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所有其他患者都在哪里?
为什么那个冬天其他地方的病毒要温和得多,而下一次致命的爆发是几个月后在意大利和伊朗——武汉是否在那个冬天经历了一种异常致命但传染性不强的局部变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最初怀疑效率如何?它传播)?
这么多关于武汉的初步报告没有意义,而且确实可能不可靠。 然而,医生的报告喜欢 李文良 关于他们如何在 XNUMX 月下旬首次在患者身上遇到病毒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
尽管存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考虑到所有可用的证据,上述内容似乎是当前对所发生事情的最合理的解释。
一个关键的带回家是它不仅仅是恐慌。 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反应代表了 2005 年出现的伪科学生物安全议程的胜利,此后一直受到组织良好、资金充足和嵌入良好的理论家网络的推动。 这些狂热分子通过在主要期刊上发表这些观点,将它们植入公共政策和法律,在媒体上推动它们并抹黑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无论他们多么杰出或有资格,来促进和延续支持严厉新方法的思想。
这种意识形态是敌人,看清它的本质是打败它的第一步。
从本文节选 每日怀疑论者
发表于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
如需转载,请将规范链接设置回原始链接 褐石研究所 文章和作者。